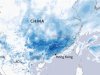谷晓丽,1981年生于河南濮阳,2004年来到杭州,7年阿里铁军生涯,“一米一粟”创始人。花名“小米”。
“阿里校友”:阿里巴巴把“离职”称为“毕业”,故“阿里校友”特指阿里巴巴离职员工。阿里有数万名“校友”,每年召开盛大的“阿里校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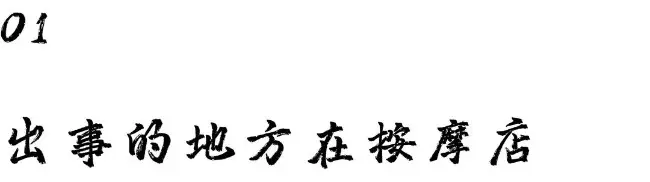
我,一个年轻女子,意气风发,在天堂杭州顺风顺水,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会以这种方式来临。出事的地方在按摩店。
这一天是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这天,我心情特别好。这天是闺蜜鸿雁(一米)的生日。我计划下午去她家玩,晚上就在她家吃饭,庆生。
早餐,我吃了妈妈烙的三个鸡蛋饼,喝了一大碗粥。我还把女儿吃剩下的粥也喝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女儿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海创园。7点,我送她去学校。
上午9点,我穿了一条白色的西裤,白色的T恤衫,外面穿了一件黑色小西装,出门去做按摩。开按摩店的是一位阿里校友(注1)。我一直想去支持一下她的生意。是那种很单纯的支持。
我带了另一个闺蜜荣芳(二姐)一起去。我们上午10点到。
到按摩店里还能干什么呢?总是先喝喝茶,东拉西扯聊聊天,然后打打瘦脸针啊,打打水光针啊,就是弄弄这张脸呗。我觉得自己太胖,还可以再瘦一点,再美一点。
技师说,你肚子上肉太多了,这是顽固性肥胖,是很难减的,你必须要用一下我们的超声波按摩仪,做一做离子按摩。
我先脱掉上衣,躺在按摩床上。仪器打在我肚子上,砰砰砰地响。
刚开始感觉还好,但是一会儿以后,我感觉肚子不舒服,要求做按摩的小姐姐减轻力道,小姐姐说这样的力道才有效果,呃,应该是宿便脱落,呆会就好了。是否宿便脱落我不知道,但我也猜测可能是因为早饭吃得太饱了。
过了好一会,肚子还不好,而且越来越疼了。小姐姐说,这应该是死去的脂肪细胞被唤醒了,在按摩过程中,多余的脂肪细胞会被唤醒、挤走,你再忍一下。
好吧,再忍一下。我的耐力总是特别好。以前经常参加那种挑战性的活动。爬山啊,杭徽古道团体赛啊,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但是我的耐力特别好,我总是能坚持到最后。坚持就是胜利啊。可这次,坏就坏在我的耐力太好。
我肚子已经疼得不得了。我还在忍。一直忍到11:30按摩结束。
从按摩店里出来,我对二姐说:我肚子像翻江倒海,难受。
二姐说:我开车,你先去我们家休息一会儿,我做饭给你吃。
于是我们就去二姐家。二姐住小和山。我们爬上5楼。她做好饭,发现我心慌气短的,饭也吃不下了,水也喝不下了。
裤子都开始紧了,紧紧勒着肚子。我想,又没吃饭,怎么裤子越来越紧了呢?
疼得不行。我打电话给那个按摩院的阿里校友。校友说,这是正常现象啊,因为你太胖了。
体内越来越热,热得发烫,每个毛孔都像是要喷出火来。我喝了一瓶冰雪碧。感觉没那么热了,但是身体还是不舒服,想吐。
熬到下午1:30。开始出冷汗。我跟二姐说,我必须得回家睡一觉。
我强忍着疼痛,自己开车回家。
开始上吐下泻。熬到3:00想起再过半个小时就要去学校接女儿。可是这时我眼前一片迷离。开始有幻觉了。
我脱了衣服上床。盖上被子觉得有点热,不盖被子又觉得浑身冷。冷汗一直冒,浑身湿透,像刚被一桶水从头到脚淋过。
妈妈认为我吃坏了肚子,得了急性肠胃炎。我想也许是那瓶雪碧把肠胃给冰到了。妈妈去药店买了一堆药回来,肠炎宁啊之类的。可是我还哪里吃得下。
我打电话给鸿雁。我说,鸿雁,你帮我去接女儿啊,我自己没办法了。
我自己打电话,叫120。这时候,我已经感觉不行了,生不如死。

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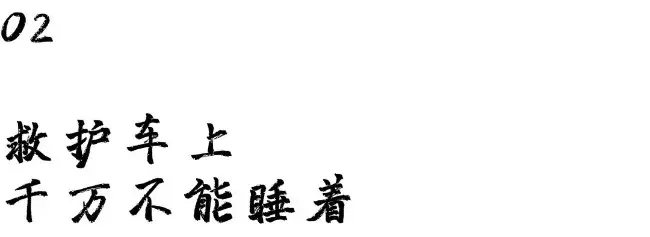
救护车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已经半昏迷。
妈妈一直叫着我的名字,一边说“车来了”,“车来了”。从我打了叫车电话后,她一直在说“车来了”“车来了”。她已经吓坏了。
救护车来了。我住公寓的一楼。一位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抬着担架直接走进屋子。
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让医生抬我走。
妈妈说:肯定得给你穿条裤子啊,不穿裤子像啥样子呢。
妈妈帮我穿了一条睡裤。原先穿的那条白色小西裤,已经紧得扣不上了。
我是清醒的,我知道身体疼,听得见妈妈焦急的声音。可我又是迷糊的,因为我已经没办法支配这具沉重的躯体。
我赤着脚,被抬上担架。只听见那位医生说:这是急性肠胃炎啊,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
女护士对妈妈说:阿姨你不要担心啊。这种病常见的,今天上午我们还拉了个类似的年轻人。
妈妈说:急性肠胃炎,她小时候也犯过,可是没这么严重啊。
是啊,起初我能听得见他们所有的对话。医生先是联系就近的西溪医院,可是一通电话后又说,那边已经成了新冠隔离专用医院,接不了急诊病人。
接着又是很多通电话,对方一听是上吐下泻发热病人,说疑似薪冠,他们不能接收。
最后,浙一医院之江院区同意接收。
司机转道往留泗路走。
这是个什么日子啊。马路上车跟车,人挤人,走不动。哦,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五,到下班高峰了,附近有所学校,家长在接孩子放学。
医生和护士轮番找我聊天:唉你几岁了?老家哪里人呀?有几个孩子呀?你在哪里上班呀?你平时都做什么工作呀?
多少无聊的问题啊!我应付了几个问题,后面就不想回答了。累极了,想睡。
护士不停地拍我的脸,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唉唉,你年纪也不小了啊,怎么没有白头发啊?我有个姐妹,年纪和你差不多,脸上褶子可多了,头发都白了……你怎么没白头发?你平时吃什么?……你这时候千万不能睡啊。
妈妈焦急地问:多久才能到啊?
护士回答说,快了快了。她摸着我的脸,说,你皮肤好白啊,你皮肤怎么这么好?
我眼皮睁不开,没有力气说话。但是我的意识很清醒,我在想:我的皮肤有什么好夸的?你是没什么好夸的了。
医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不停和你说话是怕你睡过去呢。
那段路好陡,好颠簸,整个躯体快散架了。
我努力睁开眼睛,问:怎么还没到?
医生说:你不能睡觉啊。
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我说我很冷。妈妈就拿被子给我盖上。可是被子好重了,像山一样压下来,把我压晕过去了。
再次醒来。听见医生说:快到了!快到了!前面路口左转,两分钟就到了。
妈妈也跟着说:快到了,快到了。
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你别担心,你小时候也犯过这个毛病。你会没事的。
我想,我咋不记得小时候犯过这个毛病啊?
我开始很烦躁。我觉得妈妈挺烦人的,这医生这护士也挺烦人的。这司机开得这么慢,真讨厌。
不知道啥时候能到医院。我呼吸困难。回家以后穿上的睡裤也紧了,裤带像绞索一直捆着我。完了,活不成了。
我吃力地闭上眼睛。不知过了多久,再次睁眼。还没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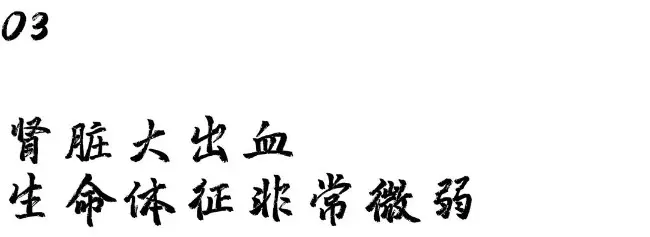
到医院发热门诊时,我已经坐不起来了。医生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说:我们马上要去接下一个病人,我们不能送你去挂号。
挂号之前,得先租一张轮椅把自己临时安顿进去。
租轮椅得扫码支付200元押金。妈妈不会扫码,在那里瞎折腾。想过去帮她一下,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我已经瘫在地上了。我感觉很无助,很煎熬。扫码租轮椅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把娘俩都难倒了。
来了一位好心人。妈妈把200元现金给他,他扫码付。轮椅租到了。我在等轮椅过来的时候,又开始狂吐。好像是真的不行了。
又发烧又呕吐的,很像薪冠啊。接诊医生让我马上做核+酸。
我坐在轮椅上做核酸检测。然后等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瘫在轮椅里,没知觉了。
啪啪啪,我被打醒了。有人在打我的脸,一下,又一下,很响很响。
刚醒来时我有点懊恼:唉呀,你这个人打我脸,怎么这么侮辱我呢?叫我名字就行了啊。
医生说:是我让他们打脸的,你不能睡着啊。
我说,我想上厕所。妈妈说,唉,你能说话了啊,太好了。
妈妈把我推到厕所。可是我一看到厕所就没有力气了,昏了过去。
核+酸结果出来了,阴性。不是薪冠。
抽血。检查。看看是不是急性肠胃炎。检查结果:肠胃没有任何毛病。
查血糖,高达26!怎么这么高的血糖?医生诊断我是酮症酸中毒,开始“对“症””下药,输液。
到了晚上8点,还是时不时昏迷。氧气包也用上了。手脚已经冰凉,血压降到了40,心跳开始急促起来。生命体征已经非常微弱。医生说快要不行了。
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最后决定,做一次全身核磁共振。
最后发现,左肾多处出血。整个腹部已经积满了淤血,肚子胀得很大。
左肾有个错构瘤,包裹着肾脏。
八年前,我生宝宝之前就知道有这个瘤,医生朋友说,它是良性的,陪你一生都没有关系,不用太介意。
上午在按摩店里折腾了一通,错构瘤破裂,肾脏跟着出血。医生说四分之三个肾脏都在出血。出血还挺快。
血再流下去,这个人肯定得挂了。必须先止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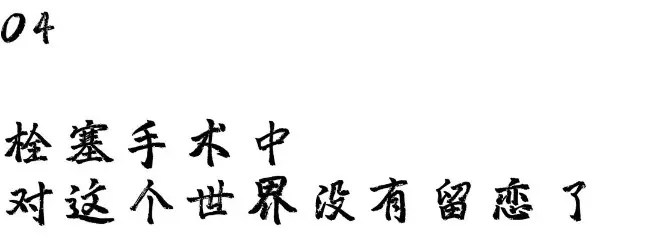
要进ICU了,得先扫码付费,还掉轮椅。
这回,妈妈直接把我用轮椅推到那个人脸识别的地方,拍拍我的脸,说:“唉,你醒一醒。”
我挣扎着从昏迷中醒来。我一睁眼,叮一声,人脸识别通过,付费成功。我一闭眼,又昏过去了。
医生说,这个病人的血管随时都有可能爆开,必须马上做栓塞手术,止血。
昏天黑地中,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吧,做手术的医生来了,把我拍醒:
“你看看,我都已经下班回家了,洗完澡准备休息了,又不得不赶回医院给你做手术!今天我已经做了很多台手术了!
“你的肾脏破裂了,血已经在到处跑。止不住,这里缝一下,那边又开了,那边缝一下这边又开了。”
被人打醒了,又听了这样的话,我好烦。唉,连医生都对我这么不耐烦啊。哪里来的这种白衣天使。哎呀,放弃吧,死了算了。
被推进手术室前,妈妈哭着对医生说:我女儿的事情……你们放心救治,不管用多少钱,我们都会付的。
妈妈一边说一边哭。我还听到了小姑子的哭声。
我被推进手术室。身后门咣当一声重重关上。医生在我身上开了很多个孔,右腿开了一个孔,颈动脉右侧开了个孔,右脚上也开了孔。左肾在出血,但要自上而下止血。
他们问我疼不疼。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的身体几乎已经没有知觉了,身体的那种疼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了。
时间好漫长,好像在手术台上躺了一辈子。长时间的昏迷。时不时被打醒。每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在手术台上。医生在打我。
医生一边打一边说:“喂,配合一下,醒醒,你不能睡啊,你要跟我聊天。”
可是我太累了,撑不住,很快就昏睡过去。医生就更重地打我,打我的腿,打我的脸,打我的手。我就努力地睁一下眼,吃力地呼吸一下。我知道医生是怕我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
恐惧消失了。想放弃。不行就不行了吧,别折磨我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了。
这肉身好沉重,要它干啥用呢?害得人家医生下班回家了又跑回来,赤身裸体地躺在这个医院里,被很多人围着做手术,还有很多人在周围跑来跑去。
从晚上9点多开始做手术,做到第二天凌晨1:30。我彻底陷入了昏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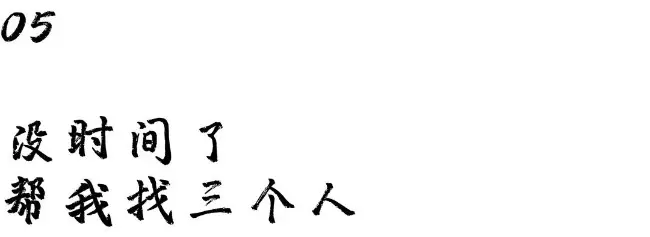
再次醒来已经是5月30日的中午了。我睁开眼睛,看见身上插满了管子,外面的天气还挺好。我奄奄一息,但是还活着。
医生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回到重症监护室。感觉好渴啊,浑身都干透了。
我说:我想喝水。
医生说:刚做完手术是不允许喝水的,你这个情况,我不敢保证会不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
但他转头对我妈妈说:“给她喝口水吧。“
妈妈听医生这么说,吓得直摇晃。
在做手术前、做手术中,这个医生一直都特别“凶”,老是要打醒我。我很讨厌他,觉得这个人特别“坏”。
现在,他居然说出了这么感人的一句话:“给她喝口水吧。”
他了解我的需要和渴望。我感激他。我突然发现这位男医生挺好的。
他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向死而生。
是这位医生,让我在绝望的边缘升起了一点点求生的欲望。
我知道妈妈不会这么想。医生让她给我喝口水,但是她拿了很多过来。妈妈一边给我喂水,一边不停地抹眼泪。妈妈的眼神在和我告别,她一定觉得我已经活不到明天了。
所有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都不让喝水,为什么让你喝水啊?是因为你活不到明天了吧,所以现在让你喝水。妈妈会这样想的。
栓塞手术做完了,肾脏出血是止住了。但肚子还是很大,胀痛,因为之前流出来的血还在肚子里,而且已经脏了。我躺着,丝毫动不了。
各科室的医生过来会诊,要不要做开腹手术,排血。
有医生说,不做手术了吧,病人太虚弱了,肚子里的那些脏血让身体自己慢慢消化。
也有医生说,这脏血身体消化不了,必须得排出来。不排掉就可能再次栓塞。盆腔、腹腔有很多积液,时间久了就会变质。
我听到了,我觉得必须尽快找人做开腹手术,把肚子里的脏东西清理掉。
左肾要切除就切除吧。腹腔里很多器官都有可能感染了。子宫可能也要切除。没关系。我可以切除所有。保命要紧。器官不重要。
要找朋友,要找一个权威的人来做这个手术。
喝了两口水,我脑袋愈加清醒。我叫道:“护士……”
护士说:“在呢。真好,你能说话了。”
我问:“手机能不能借一下,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护士回应:“你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说,我们帮忙转告。”
我说:“我只需要跟我家里说三句话。”
护士给我拿了一个手机。
我拨通了老公的手机号码。老公还在海南三亚出差,他有个节目还没拍完。
我说:“你帮我找三个人。”
老公没接我的话茬,而是关切地问我:“你情况怎么样了?”
我说:“我还好……很虚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说三句话。”
老公不响了。我说:“你帮我找三个人,请他们帮我找一个医生,做开腹手术。”
“哪三个人?”老公问。
我告诉老公,你打电话给这三人,他们都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请他们帮我找一位权威的医生做开腹手术,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如果这两个人都帮不了,就找第三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帮忙。
老公依次找了这三个朋友。三个朋友都很给力,找到了同一个医生:谭主任。

5月30日我打完电话,5月31日谭医生就来了。他在浙一余杭院区、浙江院区、庆春院区都坐诊的,都有手术。
那天上午,谭医生一上班就来病房了。正好那天我挺清醒的,我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哎今天你醒啦,这么年轻啊。”
哦,他很随和,就像是跟我开玩笑一样:“今天你醒得还不错啊。”
我说:“我没有眼镜了,我看不清您。”
“不用看我,你听我声音就好了。”谭医生说。
他一边察看我的病情,一边和我拉家常:你是哪里人啊?你做什么的啊?谁谁谁你是怎么认识的啊?你怎么这么神通广大啊?
最后他说:我决定还是帮你做手术,你交给我放心不放心啊?保命要紧,这么大一堆脏血在肚子里,你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消化完啊?
上午谭医生来的时候,我还清醒。不久我就不行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半昏迷中,我听见一位医生问:手术成功率有多少?谭医生说:三成吧。
他们以为我处在昏迷中,什么都听不到。
这种开腹手术本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谁也不知道手术行还是不行。
稍微清醒一点,我就想得很多。有时候想,手术行或不行都无所谓了,大不了在这个四十不惑的年纪,人生终止了。
还想了后事:老公还很年轻,还可以去找一个……女儿挺乖的,后妈应该不会对她太差。
开腹手术的时间定在6月1日儿童节,下午3:30开始做。这是一台加台手术。
老公已经从海南赶回来了。在推进手术室前,我忍不住对妈妈、老公说:“女儿你们要帮助带好啊……”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衣服被扒光。整个人被搁到那个冰冷的台子上。
这一天是6月1日,儿童节。我心里对自己说,如果我还能醒过来,就重新做一个小朋友。

谭医生一刀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飞起来了,飞到了上空。
我飞着,看见底下的房间里,一群男人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做着什么。那个裸体女人是我吗?我感觉有点难过。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因为突然我飞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一个人坐在一把躺椅上,不,是斜靠在一把躺椅上。大片大片的绿色草坪,五颜六色的鲜花,从眼前一直蔓延到远方,一望无际。蓝天中飘浮着一朵朵白云,时而有小鸟在空中划过。
周围没有人,面前有一道长满鲜花的围栏,是用防腐木做的。我想伸手去摸它,哎呀,我坐在那里就飞起来了,轻松地越过了那道围栏。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小花,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只是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这应该是春天的早上的景象。我的呼吸特别好,空气也特别好,一切都很美好。没有一丝生病的感觉,很轻松,很自由,一点都不累。
这是生命尽头的景色吗?好美。
可是,好景不长。美丽的世界突然消失了。
我又看见了那群男人,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很多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不清他们的脸,但听得见他们在说话。那个女人躺在台子上,一动不动。
我确认那个女人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躺在这里?为什么是赤身裸体的?感觉好丢人啊!
我突然很难过,觉得浑身冰冷。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又睁开。
一睁眼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冰窖里,我仰面躺着,胸部以下都是冰,只能看见冰窖顶部一条不足一尺宽的小缝。我浑身发冷,一动不动。
这也是生命的尽头吗?好黑,好冷。
躺在冰窖里面的,不止我一个人。
还有我老家的一个大爷爷——我爷爷的大哥。去年的时候我去医院里看过他。现在我发现他也在冰窖里。
我们俩都躺着。大爷爷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躺在我的右手边。但是我的手够不着他,他也够不着我。
我说:好冷。
大爷爷说:我也很冷。
爷爷说话的声音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我说:我们要爬到上面去,上面暖和一点。
大爷爷说:我爬不上去。
我说:要是有人给我们递根棍子就好了。
好冷啊,我想再不爬上去,可能就冻死了。
大爷爷说:我长得高,我上去了,可以拉你一下。
冰窖四周晃动着很多人影,我看不清他们的脸。有抬着东西走过去的,有空着手的,全都急匆匆的,像有急事一样走过去。
我说:这些人也不来救我们啊。
刚音刚落,冰窖顶部那一尺宽的地方垂下一根棍子,正好落在我的正上方,头上被火烧过,变成炭了。是根烧火棍呢。
我说:爷爷,我先抓这根棍子上去,再来拉你啊。
爷爷说:你先上,你还年轻。
我往上一伸手,没用任何力气,整个人就上去了。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全身绑满了绷带,插满了管子。双手被绑着。
妈妈后来跟我说,老家的那位大爷爷,就在那天晚上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