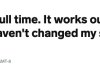2015年我毕业后,不顾父亲反对,孤身一人来到成都。
那时,成都之于我,算得上是个梦想了——或者可以说,在我那时的认知里,成都才等于是生活。
来的时候是11月,有雾。出了车站,我站在街道上,看着远处的青瓦平房和国际商业中心以一种奇异的和谐感隐在一片雾气中,仿佛整个城市的温柔都在一瞬间包裹住了我。
当我以扛着大包小包的姿态出现在这个城市时,也意识到一件更狼狈的事——父亲一怒之下断了我的经济来源,而我全身上下只剩900块了。我不清楚成都的生活成本有多高,但毫无疑问,这点钱肯定不够安身立命。
不够立命,那便先暂且安身罢。
几番辗转,我找到一家私人房屋中介,说清了自己对租房的一些基本要求:交通方便,生活便利,坏境安静,且最多能接受“套三”的单间。
中介问我:“长租还是短租?”
我答:“短租,一个月。”
他又问:“心理价位在多少?”
我犹豫着答:“……不超过900吧。”
中介用一种“你是不是没进过城?”的眼神在我身上来回逡巡,末了,拿起一串钥匙从椅子里坐起身来:“行,你先跟我去看看房吧。”
我点点头,赶紧跟着他上了电瓶车。到了地儿一看,我就傻眼了。
成都向来有“东穷西贵,南富北匪”的说法——中介带我去的房子在东三环外,地段很偏,交通不便,甭说地铁站了,连个公交车站都不见影儿。上楼后进屋一看:不足70平的小户型,居然被巧手的中介活活隔出了五室一厅一卫一厨,其余4个单间都已租了出去,只剩下最左边的一个小卧室,大约7平,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占得满满当当,转个身都费劲。
我去厨房看了一眼,水池里泡了七八个油腻腻的碗碟,燃气灶周围的油污积起来有一指节厚,各种花椒粒、胡椒粉七零八落地散在操作台上。厕所就更别提了,刚走到门口,一股凌冽的生命气息就扑面而来,熏得人打怵,探头看去,泛黄的天花板上正渗着水,马桶壁上的污渍半黄半黑,更打脑壳的是,下水口处还有一团脏纸巾,在水面上飘荡,像是糟糕透顶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中介转头问我:“你觉得房子咋样?合适的话就赶紧租了嘛。”
我说你等我缓缓,然后木然地坐在客厅凳子上。就在我发呆的空档,其他几个卧室里的租客陆续出来或做饭或洗衣、上厕所,我粗略数了下——就这一会儿就出来了七八个人。
我疑心自己看到了薛定谔的房间,愣了愣,转头问中介:“这个房子不是‘套五’的吗?”
“是啊。”
“这好像不止4个人。”
“是啊。”中介不耐烦地看了看我。他这两个“是啊”说得这般理所当然,让我完全没了继续问下去的勇气。
见我不吭声,中介抬手看了看表,有些急躁:“那你到底租不租嘛?”
我苦着脸跟他抱怨:“大哥,我虽然急着租房,可你这房子也忒……那啥了点儿吧,这完全是避开了我所有的租房要求啊,我就不说那厨房那厕所了,光这卧室也太小了吧,转个身都不行,还有这室友,这‘套五’的房子怎么住这么多人呐……”
中介大哥一个眼神冷冷劈了过来,震得我立即止了话头:“小姑娘,你可能刚来成都不懂行情,跟你说个老实话,我给你找的这个都算是不错的了。你出去打听打听,这地段的电梯房对外出租是啥价位?你想找个人少的房子,那价格肯定也就上去了,你这又是短租又没多少租金,咋可能租到‘套三’的单间?”
这番话说得毫不客气,我被臊了个满脸通红,只好问道:“好吧……那这个单间多少钱?”
“900,押一付一。”
那总共就是1800?我心里一凉,也顾不得嫌弃这儿条件恶劣了——我这点儿钱哪有嫌东嫌西的资本,今晚能不睡大街就不错了。我只好腆着脸跟中介讲了半天价,好说歹说,总算免了我押金,房租也只收了850。
收好了钱,中介递给我两把钥匙,嘱咐我“别弄坏卧室里的东西”,然后就走了。隔壁不知几号房传来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我强迫自己忽略发霉的床垫,一边把被褥拆出来铺床,一边给自己打气:出来混的,自然得随遇而安,要是嫌这嫌那,哪儿还有闯荡社会的胆气?
2
然而,我这点儿胆气很快就泄了个干净。
住进出租屋的第一晚,初到异乡的孤独感裹着四川盆地特有的湿冷,直往我骨头缝儿里钻,即便我把被子和几件大衣通通压在身上,还是冷得打颤。迷迷糊糊睡到半夜,突然被什么东西咬醒了,开灯一看——几只跳蚤正在吸我的血。
我顿时吓得瞌睡全无,拍掉腿上的跳蚤后,身体已经不受大脑指挥一样从床上弹射到房门边儿,整个人恨不得都嵌进门里去,不敢再靠近床半分。
在门边蹲了小半晚,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开始思索一个更严峻的问题:现在,我全身上下只剩50块了,该怎么活?越想心越凉,又掏出手机,把微信、支付宝里的零钱全凑在一起,好歹多出来十几块钱。
就这多出的一点钱,竟让我乐观起来:最不济,也能多撑两天了。
反正厨房脏得没法做饭,接下来,我每天早上买上4个馒头,早上吃一个,剩下的塞包里当午餐和晚餐,这样下来,一天的餐费也就4块钱。
有时实在馋得慌想吃个红豆面包,站在面包架前踟蹰半晌,都无法下定决心。店里的老板总不住地往我这边打量,眼里的警惕和鄙夷十分赤裸,叫我想忽视也不行。我先是有些羞赧,又觉着有些难过,到后头干脆起了气性——我还就不买了!直接昂头挺胸出了商店。
但光吃馒头也不行,我担心自己低血糖发作,便买了袋最便宜的水果硬糖,头晕时含上一颗,待甜滋滋的添加剂在舌尖蔓延开,我才好歹在这日子里咂摸出点儿甜味来了。
吃了半个月的馒头,一家一家地去医院人事部毛遂自荐,我总算在饿死前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家不怎么样的民营医院,工资每月1268块,幸好包吃包住,至少能让我从群租房逃离出来。
我扛着行李满心期待地住进了医院的“集体宿舍”,可现实又一次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宿舍总面积不超过30平,进门两侧,先是分别隔了两个单间出来,据说是给医院两位女医生住的“VIP房”。其余的公共面积也丝毫没有浪费,紧挨紧凑地摆了12张上下铺,给24名护士睡。厕所在外间,两个蹲位,一个简易淋浴室。
整间屋子唯一的优点是坐北朝南,采光相当好——全屋8扇窗户,却连一面窗帘都没有——看来这家医院的经费确实够紧张的。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可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断然没有退缩的道理,我只能咬着牙不去多想,住进了这间堪比香港笼屋的集体宿舍。
平日里,我们这些护士不仅毫无隐私可言,还得随时注意躲避窗外行人的目光,换个衣服就跟打地道战似的;每天洗澡得穿戴整齐排上两个小时的队,洗完再穿戴整齐走出来;自从看到有人将一双满是泥垢的运动鞋扔进洗衣机、与内衣内裤搅在一起后,我就断了好逸恶劳的念头,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有这集体宿舍的衬托,我竟然开始怀念起了在群租房里的短暂的“幸福”生活。
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个月,我就“解脱”了——倒不是我自己出来租房住了,而是医院倒闭了,具体怎么垮的我也不太清楚,总之,就是我失业了,又没地方住了。
朋友们听闻我失业的消息,都第一时间发来了“贺电”,并一致表示:医院肯定是被我搞垮的。嬉笑过后,有朋友劝我:“这些小医院也没啥发展前途,而且私人医院在夹缝里求生存也挺不容易的,还是考个大医院吧,大医院不容易垮。”
我想了想,确实是这个理儿。正巧那时全省事业单位考试临近,我便火速报名备战,最终从近千人的考试中杀出重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一家大的公立医院。
3
工作找到了,摆在我面前的大事还是租房。
要去上班的医院在一环路中心,附近房价高得令人咋舌,我自然想都不敢想,只能沿着地铁线,一站一站地去找。
那时正是三伏天,我戴着遮阳帽跑遍了地铁沿线的各个小区,问保安、打电话,爬楼看房、讨价还价,最后终于在一个老小区租到了一个“套四”的单间,面积不大,但家具齐全。
我刚按照“押一付三”交了几千房租,那60多岁的房东老太太扭脸就反口,一边沾着口水数钱,一边煞有介事地跟我提出了“三不许”政策:不许用燃气灶、不许看客厅电视、不许开卧室空调,理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用东西浪费得很,怕你们给我用坏了”。
我希望她能通融一下,老太太还是坚持这套说辞。我的急性子又炸了,懒得跟她掰扯,便直接说:“我不租了,钱退给我。”
这下那老太太却不依了,捂着口袋,摆出一副我拿她没办法的嘴脸,就是不肯退钱。拖了两三天,非要讹我几百块“人工费”,才把剩下的钱退给了我。我虽恨得牙痒,也只能当破财免灾,拿了钱又重新开始找房。
后面的一周里,我没日没夜地在各大租房网站上筛选合适房源,可网站里大多是虚假信息,看上一间出租屋,电话拨过去,中介总会信誓旦旦地保证房子还在,可到了地儿,他就立马“遗憾”地表示:“你早来一步就好了,那个房间刚刚租掉了,要不你跟我去看看附近的?”
不用想,他带我去看的,自然都是些地段偏、硬件差、没人租的房子。
一次,中介带我去一个刚翻新的老小区看房,里面空无一物,正要转身走人,中介却劝我:“正好家具刚拉来,你帮我一起组装好了,再看看整体效果,到时候你肯定觉得大不一样了。”
不知咋的,那一刻我竟跟被下了降头似的,傻傻地花了半小时、费了吃奶的劲儿帮着他组装好了一个两米的木床和衣柜,弄完一看——“这整体效果好像跟刚刚没啥区别啊?”
“哎呀,你实在觉得不得行就算了嘛,我也不强求你租。”中介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突然明白,敢情自己是被当免费劳动力使唤了。
颠沛流离了小半个月,我总算通过中介租到了房——是个电梯小区的“套三”次卧,房子就在地铁口附近,离医院5站,周围生活设施也算齐全。
房子是租到了,日子却依然过得不舒心。搬进来后,我才发现,自己租的这个单间正斜对着隔壁住户家的客厅窗户。为了保证自己在这个城市暂时且唯一私人空间的私密性,我只能不再拉开窗帘,过上了吸血鬼般不见阳光的日子。
房间狭窄,终日不见光,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被禁锢在一个小盒子里,一度憋得抓狂。可就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我一住就是两年。以至于后来谈到买房,朋友问我:“你对你以后的房子有啥憧憬么?”我总会毫不犹豫地答道:“只要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就行。”朋友们纷纷取笑我没追求,我也只是讪笑。
由于房间小、没空调,我也不敢买大件儿——一是放不下,二是搬家麻烦。我从附近家具店扛了台塔扇回来,在逼近40度高温的成都,塔扇降温的效果杯水车薪。无数个暑气熏蒸的夜晚,我一遍遍拿过了凉水的毛巾去擦竹席,擦完躺上去没两分钟,身下那片儿就又开始发烫了,我只能不停翻身换地儿,跟烙煎饼似的折腾半天才能入睡。
至于同居的女性室友,一开始我还怀着热情跟她俩谈天说地、请客吃饭,可她们到底只是随聚随散的过客,流动性太大,一来二去,我也淡了心思。白日里的工作已透支了所有力气,等回到这个唯一的隐私空间,实在是连半分热情都欠奉。我逐渐发现,还是跟室友做个陌生人最简单——不用交际,泾渭分明,彼此都落个轻松痛快。
等后来,租客不断更替,我跟她们也默契地保持着冷漠,且绝对避免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里。日子一久,我听声辨位的功力大增,偶尔预判出错、跟她们撞上,也只是不动声色地各忙各的,没有虚伪的寒暄,更无一丝视线相接的可能。
4
我一直记着自己选择来到成都的初心——简单地说,这里就是我对生活的所有梦想。可“漂”久了,却叫我不敢十分肯定这一初心的正确性了。
一晃已经是11月,护士长给我一周连着排了四五个夜班,每天凌晨从医院走出来时,我就立即用口罩掩住青白的脸色,昏昏沉沉地汇入人潮。整个城市都笼在灰扑扑的雾霾中,路上行人也都带着口罩,看不清神色,只是垂着眉眼埋头赶路,像流水线上的人形木偶。
我忽然意识到,来成都已经一年了,我还没能捕捉到这座城市的光影、描摹出它的筋骨脉络,却已先被它的生存压力绊了个趔趄。
流动的陌生邻居、逼仄憋屈的出租房、日夜颠倒的高压工作,跟大多数在大城市奔波的年轻人一样,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出租屋和工作之间。白天在急诊重症病房里绷紧神经忙前忙后,下了班,还得拖着空荡荡的躯壳去挤成都的“死亡专线”——排上半小时队,被蜂拥的人潮推入车厢,被挤得双脚几乎离地,在车身的震动中努力保持着“我自岿然不动”的状态。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亲近”这个城市。
很快,出租屋里的另一件事就直接激怒了我。
最初租房时,中介跟我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绝不会有男租客住进来”,叫我放心。可一天,等我下了夜班回到出租屋,却见一个年轻男人正从2号房里走了出来,一见到我,立刻扬起黝黑的脸,冲我友善地笑了笑。
我笑不出来,直挺挺地僵在原地,怒意迅速蔓延到全身。我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竟恨不得把所有怒意全灌进这眼神里,再齐刷刷钉进他肉里。
那男人愣住了,显然不明白我的怒意从何而来。我没管他,以最快速度掏出钥匙开了房门,再关上反锁,整个人用力往门上抵,震得脊背生疼。
我很快拨通中介电话,劈头盖脸就质问他为何出尔反尔。中介却不甚在意地跟我打哈哈,说他也无权限制租客性别。我气愤至极,还没继续和他理论,眼皮就开始发烫,豆大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掉。
这些中介整日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早就活成了人精,我这种刚出社会的小姑娘在他面前根本不是个个儿。他三言两语便将我打发了,很快挂了电话。再拨过去,就只有冰冷的电子女声。
我一时心乱如麻,一想到自己要跟一个底细不明的男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且不说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万一他起了歹念,我该如何应付?我又开始夜不能寐,每天挂着一双青黑眼圈,搜索各种女子防身术、如何发现屋内隐形摄像头,枕下还搁了把水果刀防身,常常在脑子里演习着所有有可能的危险状况和一招制敌的策略。
我也曾想过搬走了之,可眼下刚交了几个月的房租,中介自然不愿退钱,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住下去。
好在时间久了,我发现他对我也并没有任何威胁,也就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毕竟我们平时从不打照面,从不交谈,除了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算得上是没有任何交集。
后来某日我刷知乎,看到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女生愿意跟男生合租?”再细看下面的“问题描述”,字里行间全是对与男生合租的女生的不满和诘问。我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出于什么心态,但说起来,我们都不过是被生活推着走的蝼蚁小民,又哪能有那么多选择和事事顺遂。
过了几个月,这个黑脸男人也就搬走了。
5
2017年年底,2号房住进来了一个30出头的失业男人。在此之前,从刚毕业的小姑娘、到敲代码的程序员、再到一对年轻夫妻,这个房间的租客已经来来回回换了好几茬了。
有了之前跟男租客们合租的经历,我对他倒也没有格外戒备,照样过着自己两点一线的高压生活。
大年初五,我从老家返回成都,到达成都已是傍晚,街上千家万户灯火通明,欢声笑语隐隐传来,好不热闹。我披着一身倦意回到出租屋,正掏出钥匙准备打开卧室,却没找到熟悉的锁眼,登时被惊出一身冷汗——锁被撬了!
慌乱过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俯身朝锁眼看去,里面的锁芯已碎了个干净,一半留在锁眼里,一半零零散散掉在门框下。我伸手把地上碎掉的金属粒一点一点抠起来,放进掌心仔细打量,凉意瞬间从脊柱缝里涌出,爬满全身——我清楚地记得,我走时锁芯是完好无损的,现在碎得这样彻底,只能是人为。
1号房的女生还未从老家回来,除了是2号房的那个男人所为,我想不出别的可能。
听着2号房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动静,我心下一惊,立刻打了门冲进去,再把门紧紧关上。大脑空白了好几分钟,我才回过神来,赶紧四处查看有无财产损失。
令我疑惑的是,所有东西都在,并无失窃。我一时没了主意,本想打电话报警,可一来并无失窃,二来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实证,警察来了,肯定也只是做个笔录就走人,万一激怒了那个男人,等警察一走就对我打击报复怎么办?
出去住酒店也不行,屋子里好歹是我的全部身家,现在门锁不上了,我一走,万一真失窃了怎么办?
偏偏此时又是大年初五,联系了几个朋友,都还没返回成都。打电话给锁匠,也都还在老家欢度春节,我最后的求助机会都没有了。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困境:出不去,待不住,进退维谷。
时间一点点流逝,夜色铺天盖地涌进房间,将我淹没。我按下电源开关,昏暗灯光亮起,钨丝灯嘶嘶作响,一声声锯着我的神经。我捏着水果刀坐在灯下一动不动,看着自己的影子凝在地上,像个张着嘴的黑洞。四周黑魆魆的,一片死寂,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太阳穴处血管的搏动,只有窗外街上偶有汽车驶过,轮胎与柏油路摩擦的声音被黑夜放大。
枯坐了大半宿,我实在熬不住了,强撑着精神,将衣柜和桌子推过来抵住门,裹着被子蜷在桌上睡了过去。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中介要求退房。
虽然租房合同也差不多到期了,但想要全额退押金却是不可能的。中介公司找了多个拙劣借口,将我的押金扣得七七八八,最终象征性地退了我23块钱。
我急于找下一个住处,也不想跟他们多掰扯,马上又开始在租房网站上搜寻下一处安身地了。
6
这一次我运气挺好,当天就在西三环外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所——虽然地段略偏,房子也有些老旧,但好在是个“套二”的出租房,租客只有一个女生。一付完房租,我立刻打包了所有行李,联系了小货车准备搬家。
六七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装满我所有家当,我帮着司机将行李全部扛上车,坐上副驾。等到了小区大门,车却被拦下了。门口保安挎着电棍,警惕地绕着小货车看了半晌,语气不善:“你们这搬家,得先去物业那儿开个通行条,不然不许出去。”
我掏出租房合同给保安看,又说了半天好话,他依旧不予放行。司机安抚我:“你去物业那儿开条吧,我保证不得把你东西拉起跑。”我只得下车快步往物业中心跑去——说来可笑,我还当真担心司机将我所有家当给拉跑了。
10分钟步程,我一路疾跑只用了3分钟。可到了物业那儿,居然又遇到了一场无妄之灾——虽然我租房两年的所有费用都已给中介缴清,可中介竟已5年未缴物业费了。了解我的来意后,工作人员给业主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放行,业主明知我的租期只有两年,却在电话里径直要求我先替中介缴清5年物业费,否则就不让我走。
我连忙打电话给中介,那边却就开始推脱责任,还说叫我自己跟业主协商。可不论我如何解释这事和我无关,物业和电话里的业主都一口咬定——不管是谁,必须先交钱。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陆续有牵着孩子、提着菜篮的住户走了进来,物业又立即迎了上去,满脸春风地向住户们介绍着最近换门禁卡、扫码领奖品之类的活动。空荡荡的物业中心一时热闹起来,可我独自站在大厅一旁,只觉得如同置身荒野、四面来风。无形中像是有一道壁垒,将我与他们隔离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租户”,一边是“业主”,泾渭分明。
我掏出手机给小货车司机打了电话,告知他这边的情况,可没等一句囫囵话说全,就鼻子一酸,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一边哭还一边不停警告他:“不许把我东西拉跑了。”
司机大约觉得我很是莫名其妙,只说了句“那我先等着吧,你等会儿得加一百块钱”,便挂了电话。
许是见我哭得太有碍观瞻,工作人员终于招手将我叫了过去,然后把盖了章的通行条交给了我。
好不容易搬完家,我才开始细细检查起了房子:阳台栏杆上油漆剥脱,已翻出了大片的铁锈色;立柜式空调的扇叶上也长满了灰毛,送出的风都裹着浓重霉气;房间锁的质量欠佳,螺丝松动……
我买来所需物品,然后全副武装,开始动手刷油漆、清洗空调、换锁、疏通下水道,弄完这些,再开始整理床铺,抬起床板,却瞬间头皮发麻——床下的空隙间密密麻麻全是蟑螂。
这些美洲大蠊,个个通体油亮,擅长飞行,一只都够让人抓狂的,何况这一大窝?我还没从恐惧中缓过来,几十只蟑螂就已飞速爬了出来,有几只甚至从我脚上爬了过去——那种触感,终生难忘。
我强忍住想要截肢的欲望,立即退出房间,深吸一口气,正式开始了除蟑大业。
到底是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年的王者生物,想要将它们这些蟑螂消灭干净,着实不易。我用硼酸将全屋清洗,各角落放上饵剂、再喷杀虫剂,门缝全用泡沫垫子堵起来作为门挡,卧室门口也洒了一圈硼酸划出安全区。即便这样多管齐下,我还是没能彻底清除这些恼人的蟑螂,原因无他——室友太不爱干净了。
多番劝说无效,我又只好做起了家庭保姆,包揽了所有倒垃圾、扫地拖地、定期除虫的工作,最终也算卓有成效。
卫生问题解决了,新的麻烦又来了。
没过两个月,室友谈起了恋爱,开始频繁地将她男友带回出租屋。有次我一开门进去,就看到他俩跟连体婴似的抱在一块儿动情亲吻,亲得忘我,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他们的嘴都拔丝儿了,我赶忙扭身开门进了自己房间。
而之后的事才真叫一言难尽。
说起来,这对脾气火爆的情侣也挺有意思,往往凌晨两三点万籁俱寂时,就像狼人一到月圆之夜就要变身一样,毫无预兆地就拉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每回都是我睡得正酣,一声惊天动地的狮吼就会瞬间把我震醒——这便算是他俩正式开战了。开战后,上来先是一阵狂风骤雨般的骂战,骂架也不带重样,一般先礼貌问候对方的祖宗十八代,探讨“X你大爷”、“X你娘”的伦理问题,再自由搏击半小时,然后就是跺脚捶墙,消停没两分钟,居然又发出生命大和谐的声音。
我头昏脑胀地听着隔壁的动静,实在惊讶于他俩这起承转合毫无章法和逻辑可言。
这样的次数多了,我也忍无可忍了。一次,又是凌晨两三点,我看他们还不消停,便从床上爬起来,假意上厕所路过他俩房间,然后大声咳嗽以作示警。
谁曾想,我明示暗示了个遍,他俩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大,颇有战死方休的气魄。我只得拖了条凳子坐到房门口,然后掏出手机开始放歌——《新闻联播》的片头曲,最大音量。在这庄严肃穆的歌声中,隔壁这才终于渐渐偃旗息鼓。
我原以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结束——谁料我回了房刚一躺下,隔壁又开始哼哼唧唧起来。我心想:有种你别停,我且放个《郭德纲相声全集》给你们助兴。然而这兴到底是没助成,被他们闹了大半宿,我脑袋昏昏沉沉实在困得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自那后,隔壁的确收敛了不少,我也不再计较,半夜再被吵醒,也只当听个有声小说了。
7
搬了数次家,跟各种室友斗智斗勇,虽然一地鸡毛,日子却也都这样磕磕绊绊过来了。
转眼到了2018年年尾,我辞去了医院的工作,转行之路又困难重重,一时茫然,整日闲居出租屋内无所事事。父亲打来电话,勒令我在春节之前回家——说是家里已经替我找好了医院,年后就得去上班。
想来人生许多大事小事最终落锤,也就都在春节前。
父亲软硬兼施,我却迟迟不愿答应,我不想重新回到被他规划人生的日子——父亲向来强势独断,我从小到大的所有事皆由他做决定,容不得我置喙。
见我油盐不进,父亲顿时恼了,说话也带了刺:“你一个人非要去成都,大城市就那么好吗?我们这种小城市容不下你是怎么的?你认为你自己是拿得到成都的户口还是买得起成都的房?未必你想在成都住一辈子的出租屋?”
我只能沉默以对。
在成都的这第三年年尾,我开始回想那些自己在这个城市挣扎生存的日子,以及决意要来成都的初心,却始终像是有烟雾缭绕,看不分明。
我想起之前那逼仄、不见天日的出租房,想起搬家找房被坑的种种经历,想起吃到吐的外卖、流动的陌生室友、飞涨的房租,一时竟生出“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我忽然才意识到,我在这个城市的所有跌跌撞撞求生存的片段,似乎拼凑不出一个可能的未来。
可又转念一想,生活不就是这样么?这世上本就没有一眼能望到底的清晰坦途,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罢了。哪怕这河过得跌跌撞撞,哪怕被这人间烟火熏得灰头土脸,好歹也算是实实在在活了一遭。
“我还想待在成都试试。”我这样回答父亲。
说这话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的合租生涯,还远未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