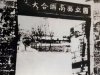编者注:本文节选自《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言部分。
乘着桃源划子那样的小舟,由常德转走沅水,舟中仅竹简、绢笔、玉剑及手编的楚国宪法。两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这样消逝了。沈从文说,沿江可见娱神歌呼与火光,岸上是《长河》中的红色橘林,于是有《橘颂》传世。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道橘红伤疤。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赖。南朝诗人谢庄《怀园引》诗曰:“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怀乡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种心灵温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断肠草有毒,“条条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雾多,浸润游侠精神与传奇志怪气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人人洁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木竹环伺的乡里村寨,山歌喂养的灵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轮回的水车,便是沈从文的乡下人世界。

沈从文在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在水边,在船上或在炉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悯、人世可亲的字句,想象力也燃烧起来。他的寂寞像是在给什么东西下跪,落在纸上时是与人世共苦乐的挺拔样子。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做小说的一份诚意。

记忆,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个地方,要经过细节的唤醒才好识别。在荷马的世界里,“忘记”是生命中最负面的动词,奥德修斯的意义,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存记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为沈从文传记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语读者理解的同时,意在渲染沈从文的“史诗”性。奥德赛,意指旅程,而奥德修斯无论曾经代表什么,他首先是个敏感而痛苦的人。沈从文与奥德修斯都历经漫长的山水险途,他们的得救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人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作为一种通用的介质,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时,深暗的水(黄泉)还带来死亡的教诲。沈从文或许是那个时代亲历可怕现场最多的作家,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爱、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却几乎与宗教无涉,这是一种厉害之至的写法。
死亡将生命一劈为二。死亡既是命运,也是一份厚礼,它的绝对性让人肃穆起来。死是人类共有的处境,死的痛楚传递着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烛光徐徐燃尽的人”。他分享故事,读者获得温暖。本雅明认为,这份温暖是双向的。对叙事者而言,死亡是他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同时,借助这个不可辩驳的自然流程,叙事者传递着生命之火的温暖。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死,犹如一团燃尽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们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颤抖的自我:
小说富于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时常稍带教诲,向我们描绘了某人的命运,而是因为此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
中国思想的紧要处是“易”,而活泼处在“禅”。变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经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于忧患境遇,于是由知警而开悟。禅语禅意是经验性的,多植根于烟火民间,如流行的口头禅或俗语。两种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铺陈出独特的中国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后而求变,他说,“我想读好书救救国家”;另一方面是敏感于一切反常的新旧经验,他说,“进步正消灭掉过去一切”。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narrative supplement)。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archive)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准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文学与律法,历史与故事在水边“聚义”,纳的投名状却是乡评与记忆——溪边的三三,桂枝的草药,伍娘的灶台,凝视火焰的樵夫,疯癫的山鬼,躲进丛林的猎人,半夜里为儿子哭泣的母亲,当然,还有生命最后一晚仍舍不得点桐油灯的“颠东”孤老。
沈从文笔下“无呆相”。《景德传灯录》有一则禅宗公案: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机锋不宜说破,人要自悟,要访师拜师,要“行脚”,在刀山剑树中或迷,或悟,如此才亲切明白。所谓公案,是不愿对“大问题”表态的意思,敲在头上的棒喝故事大多与“公”无关,而是描摹不同问答状态的个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较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
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文字是人类对居家感的确证,石刻岩画中多以水火或围猎场面为意象。一个被称为“家园”的地方,不仅是一幢漂亮楼宇,还意指着某种心灵状态。那是一个用火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炉火边遐想的地方。用火点燃柴草,炉火就温暖家庭。围绕篝火与灶台展开的,是记忆和经验,是生火、拨火的技艺,它培养人的耐心、胆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说,“我宁可旷一节哲学课,也不愿错过早晨起来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拨火是一件耐心、大胆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契诃夫的《在峡谷里》写乡下姑娘“丽帕”受尽凌辱又失去孩子,她问邻居:“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众人无话可说,默默坐了一个小时。一位老人开口道:“我们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上帝不让鸟儿生四个翅膀,只让它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让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让他知道一半或者两三成。”接下来,老人讲了一个故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我到过黑龙江和阿尔泰山,我在西伯利亚住过,后来我想念俄罗斯母亲,就走着回来了。我记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一块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爷瞧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说,“治不好的病,就是命运了”。人与人在苦难中得和解,得安慰,这或许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种人类关系。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