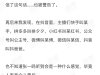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成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