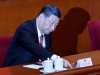台湾和美国都不约而同开启了“2024年总统选战”,各党都进行候选人的遴选。在台湾,民进党早就定于一尊,但国民党却进行激烈的竞争,而成功企业家郭台铭(郭董)更非常努力争取代表国民党的门票,很认真的提出诸多政见期待得到认同。尽管事与愿违不被提名,但他提出的“普遍将CEO精神注入行政管理系统中”或者“企业家治国”的理念或主张,却很值得一谈。
企业家治国妥当吗?
郭董明确表示“一个CEO面对的是最严苛监督,是自己所订定的经营目标,是否能达成,有非常明确的检验项目与指标,是种自我内化的要求,没有这种自我要求,不可能在激烈竞争的企业界立足”。他还说他是“表达对行政首长的更高期待,而议会监督是天经地义的,但那是最低标准。以经理人精神参选,从政的人,不应只停留在满足议会监督的标准,而要有比这更高、更难达成的标准。”这是郭董的信念,是他毕生当CEO的态度,提供和所有想从政者共勉。
乍听之下,郭董的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治国”和“经营企业”或“经商”会是相同的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在1930年代初对“厂商运作或管理”深感兴趣,他有一个根本的疑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其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1928年才实行的,列宁这样说过:“在共产主义下,整个济经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有些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在西方世界却有不少大工厂,那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就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1931年寇斯带着这些疑问赴美游学一年,拜访了社会主义领导人和福特(Ford)汽车、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并且访问了一些大学,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游学一年结束之际,寇斯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虽仍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他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解答。
寇斯觉得,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经由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却忽略了市场运作仍有其成本的事实,而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应该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寇斯清楚知道,以此方式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的观点。不过,我们却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有时则是透过市场协调。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高低来决定。
1932年,寇斯开授一门“企业组织”,自己准备授课素材,并且对自来水、瓦斯、电力,尤其对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一系列的历史研究。1934年21岁时,寇斯撰写了〈厂商的本质〉(The Natural of the Firm)草稿,将他授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经一番修改后投稿到《经济学刊》(Economica),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五十年之后才大放光芒并成为寇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该篇文章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这个重要概念。
国际知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就以“交易成本过高”来回答“一个国家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这个论题,而中央计划共产或集体所有产权制度,光是督导从属的这种成本,就远比在私有企业或市场经济下许多成本的总和高得多。这也就是说,CEO治国,把国家作为一家大厂商来经营会是很糟糕的。
两个陷阱:公营企业与私营政府
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谈“企业家治国”。在“台大四人帮”(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四位台大经济系教授)合著的第一本最畅销、“最本土化”入门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上、下册)》七版下册“31.4中国经济制度转轨”中“两个陷阱:公营企业与私营政府”里,疏理“中国是什么经济制度?”他们以“经济制度分类的本质: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与程度,亦即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疏理这个问题。
他们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是由私人经营企业,在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透过价格的调整,指导供需双方,达到社会最大的经济福祉。而政府则因有公权力,所以从制度上利用宪法制定政府组织的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与制衡,以及明定人民基本权利不得侵犯,来节制政府的公权力。由于基本性质的不同,市场要放任私人自由,以发挥最大的价格机能;而政府则需要有健全的制衡,才可以发挥功能,又不会弄权滥权。”
政府经营企业,就是公营企业,很少看到做得好的,1990年代全球就出现“公营事业民营化”(privatization)潮流,而共产主义经济崩溃也缘于此。
相反的,若公权力放任私人使用而缺乏适当规范,就是用强制力施加于别人,这其实就是强盗。如果政府把公权力任由没有规范的官员使用,结果比强盗更坏,因为等于是“合法的强盗”。
他们认为,中国从1949年建政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刚好掉进了这两个陷阱:1978年以前是政府全面掌管农工商业的“公营事业”体制,1979年变成政府官员使用毫无节制、毫无规范的公权力,像私人经营事业那样谋利的“私营政府”体制。
如此一来,从“公营企业”转换为“私营政府”,前一阶段成就了一个最不好的经济,后一阶段变成一个最不好的政府。
他们称这是两个陷阱,最根据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经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中的两句话而来。这两句话是:“商人性格与君主性格之两不相容的程度,那是无以复加的了。假若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为极坏的君主,则君主的精神,也同样会使其成为极坏的商人。”(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 If the trading spiri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enders them very bad sovereigns; the spirit of sovereignty seems to have rendered them equally bad traders.)
他们认为第一句话是说:“从没有任何两个性格,像商人(市场)与君主(政府)那么不搭调。”而当经济学谈到“市场”时,就是“没有政府干预”的意思,毕竟市场与政府在方方面面都是对立的。第二句话是说:“如果(我们让)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去掌管政府公务),使他们成为烂透了的政府;那么,政府去经营企业,也一样是烂透了的企业。”十八世纪英国政府赋予在海外的东印度公司许多政府的职能,而东印度公司滥用了这些权力,成为非常坏的政府。史密斯借用这个事实,预期政府经营企业(公营企业)的悲惨后果。四位教授举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也有相同看法,因为洛克有句先见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他们再指出,己经知道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把所有企业收归国有,成为全国都是公营企业或“政府企业”,结果是一个“烂透的企业”,而且所有共产国家都因此导至政府解体。那么,用这个盖棺论定的事实,去推论“改革开放”后仍继续维持一个不受制约的专制政府,像私人企业一样经营政府(私营政府),它必然会是一个“烂透的政府”。
他们认为,今日的中国官场,腐败已从“个人腐败”升级到“组织化腐败”,再升格到“制度化腐败”。民主国家不免有个人腐败,把腐败份子绳之以法,腐败就结束了。若是组织腐败,那就是整个单位从“一把手”全体腐败;这时,要解决问题,就是重组单位。但在今日中共的“制度腐败”,纵横交错的腐败、官官相护,除非整个制度解体,已经无药可救了。
其实,郭董最初提出CEO经营政府,是说要废除议会监督的,是经过排山倒海的批评之后才改口说议会监督是天经地义的,这根本是应付讨好的违心之论,毕竟CEO(或个别商人)是希望透过“独占地位”限制生产与供应以获超额利润,是不受监督的,美其名是“自我监督”,其实是独裁、专制。
“官僚制”公部门与“利润制”私部门分工合作
我们再由公部门“官僚制”、私部门“利润制”的角度来看“CEO治国”或“商人政府”。
奥国学派巨擘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1944年出版《官僚制》(Bureaucracy)这本书,很明显是眼见欧洲已被社会主义攻陷,而美国1930年代实施“新政”以后,政府干预市场的事件愈来愈多,而且是在民意认可下为之,但还未到积习难改的严重地步,还有得救,于是赶紧提笔引用将法、德、俄等经典官僚主义国家的经验,凸显出社会主义实施的严重后果,委婉劝说美国人民不要继续给政府愈来愈多干预市场的权力,要相信“消费者主权”的资本主义,不要相信“政府全能”的社会主义,赶紧回归1776年美国创国的传统—自由经济资本主义。
米塞斯在书中并未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官僚制”、“官僚”为何成为骂名、被负面看待。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里,官僚或政府官员虽口头上称“公仆”—人民的仆人,实际上是在“管”人民,因其有“权力”,除非道德高尚的人士,否则难免落入“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漩涡中,而贿赂、贪腐、官商勾结、黑白挂勾、合法掠夺等等现象会层出不穷,而“特权”、“特许”的“寻租行为”(rent seeking)也是家常使饭。即使没有这些弊端,由“铁饭碗”、“金饭碗”这种对公务人员的职务称呼,就知道保守、不思进取是必然的,而社会就不太可能向前进了。
经由米塞斯的透彻分析,我们应可了解官僚制的真义,也明白政府或公家机构非用官僚制不可,而民间营利事业则用利润制,即使是“自然独占”的企业也是。不过,民间非营利机构还是用官僚制。乍看之下,似乎利润制优于官僚制,其实两者无法作比较,只能说民间营利机构或事业,是可在两种制度间作选择,很自然的会选用利润制。
既然政府或公家机构非用官僚制不可,那么CEO或商人来管理,就会如史密斯所言,会是一个“烂透的政府”。所以,基本上不是谁来治理政府,而是要让政府小而有能,不可以让政府管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才是正办。
说到底,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充分发挥,而政府充其量只从事国防、治安及建立“法制的社会秩序”任务,是最能福国利民的社会。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市场机能”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是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换个角度说,对人类最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利润制,绝非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中央集权、政府高度管制的官僚体制。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