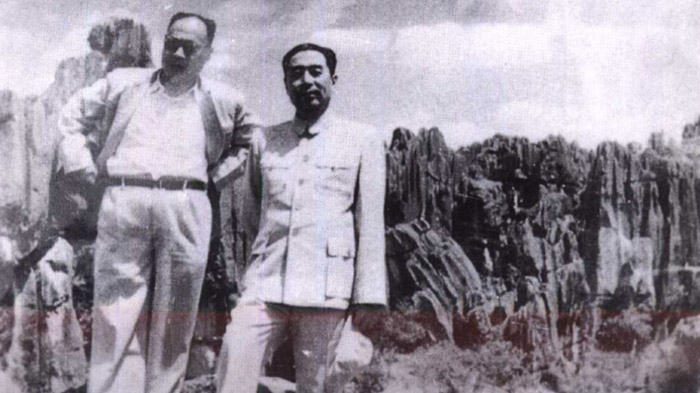
中共要角无高知,一处很有意蕴的风景。建党之初,因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苏联,缺乏多元容异,一些高知早早退出,如李达、张申府。等到陈独秀也成了“不同政见者”,竟然连他也遭中共开除。
周恩来
赤潮入华,其暴力与极端的价值指向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社会接受,仍有一个渗透漫延的过程。1921年1月30日,留法生周恩来(1898~1976)动摇于激烈俄式道路与温和英式道路之间——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1]
此时,青年周恩来虽尚未左翼化,但其对国家形势的判断——“吾国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已清晰暴露年轻人急于求成的躁动心态,决定他有接受暴力赤说的客观基础。
青年人一般屁股都坐不住,不期然而然地极易滑向暴力革命。了解周恩来的同学、朋友都说周不适宜走学术道路。1912年,14岁的周恩来向往留美,报考清华学堂,未通过英语考试。他自己也承认: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2]
1916年10月南开中学《敬业》月刊第10期,周恩来撰文自谓:
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3]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留日,两次争取官费资格的考试皆北。[4]1919年9月入南开大学,承认没读一天书,全身心投入五四运动。1920年11月留欧,在雷诺汽车厂“勤工”仅三周(100法郎/周)[5]就干不下去了:“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6]
1922年3月,周恩来致函国内南开“觉悟社”友人,说他1920年底赴欧初期“谈主义,我便心跳”,对激进主义还有一定排斥,1921年秋才铁了心追随共产主义。[7]
周恩来晚年对侄子掏吐肺腑:
我参加革命既是自己的深思熟虑,也是被逼上梁山。[8]
陈毅、刘澜涛
陈毅也是五四后赴欧的留法生,他与一批不想打工只想读书的华籍学生冲击驻法领事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遭强制遣返,参加中共也属“逼上梁山”。陈毅性格直率,快人快语:
原想做人上人,步入上流社会,想到法国读博士,不料书没读成,反被赶回国,无奈之下才去干革命。[9]
进入中共,纪律第一,中共最欣赏的是刘澜涛式的干部。刘澜涛(1910~1997),陕北米脂人,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1950年代初为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部下吴江(1918~2012)评点——
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叫向左就向左,叫向右就向右。他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达到盲从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但缺乏必要的创造力和决策能力,大政方针都取决于第一书记或听从党中央。他是“唯上论”的忠实奉行者。[10]
中共领导层的小知化,任何一个细处均可得印证,如中共要角回忆录无一注释(即便涉及重大决定与数据),毫无取信于人的基础意识,一副霸道的“我注六经”——我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相。李维汉、薄一波、林彪帐下虎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历史歧点
高知经历相对丰富、见识相对深该,对共产主义有能力作出理性预判。1930年,胡适对共产主义有一段清晰认识:
狭义的共产主义者……武断地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11]
但此时的胡适,虽有大名,但因其温和态度,甚不合青年学生的激烈口径,其声其音已是嗡嗡蚊吟,没多少青年要听了。青年李慎之(1923~2003):
(我们)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12]
1925年“五卅”后,18岁的王凡西(1907~2002,后为托派):
胡适之、梁任公思想已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完全站稳了左派的陈独秀立场,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入共产党。[13]
1925年初,夏衍(1900~1995)在日本经孙中山批准,戴季陶、李烈钧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4月下旬,夏衍转入中共。[14]
这代青年意识不到他们的这一“进步”——远胡适而亲鲁迅、远“国”亲“共”,正是别温和而亲暴力的风向标。马列赤说使中国意识形态渐离中庸急趋极端,成为关键性的历史拐点,最终导致大陆赤沉,走向暴力土改、血腥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黑文革、六四……直到今天“反潮流”的恢复终身制。而欧美之所以最终摒拒马列赤潮,甩脱呼啸二十世纪的赤难,所倚所赖还是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及时识穿马列的荒谬性,不像落后的中苏,只能痛苦地实践证伪。
2019-1-9 Princeton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合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8年,页8。
[2]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01。
[3]《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页240
[4]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王弄笙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5。
[5]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09、33。
[6]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11年,页74。
[7]《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1922年3月致函谌小岑、李毅韬。
[8]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11。
[9]黄嫣梨:《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页172。
[10]《政治沧桑六十年:吴江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50。
[1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12),载胡适:《胡适文选》(朱自清点评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13年,页47~48。
[12]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笑蜀编:《历史的先声》,香港博思出版集团2002年,页20。
[1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1980年,页13。
[14]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15年,页5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