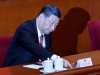夜晚的颇章布达拉
前些日子在推特上看到一个视频新闻,是俄罗斯的一位宣传员安娜·多尔加列娃(Anna Dolgareva),带着平静的表情和平静的声音在电视节目中平静地说:“……所有抵抗的乌克兰成年人的身体要被消灭,他们的孩子要在俄罗斯精神中长大。”她的话印证了另一篇报道:据耶鲁大学公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报告揭露,俄罗斯在其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关押了至少6000名乌克兰儿童,并且可能更多。报告称,“俄罗斯联邦承认的多个营地被宣传为‘融合计划’,显然其明显是将乌克兰儿童融入俄罗斯政府的民族文化、历史和社会愿景”。
我于是想起我的一篇文章,是从我写作多年尚未完成的长篇家族故事中选摘,题为“蛮子的舌头”,关于我及同代族人被驯化的经历之回顾: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并没有意识到汉地与藏地有什么不同,也没有预料到我会与自己的家园、所属的文化渐行渐远。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藏语它叫什么呢?),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当我们下车,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街边饭馆前摆放的盆子里,堆满孤零零的兔头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一时发愣,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会变成豁嘴的西藏民间传说,眼前也出现了那穿过高山纵谷的道路上,藏语发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绝不会多出另一本藏文课本或彝文课本。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后来,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3月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可是,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啊,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
二十年后重返拉萨的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我。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但万事万物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我之所以被置换成另一个人也是有原因的,正如西藏的一句谚语:“鸟落在石头上,纯属天缘”,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换掉心脏。
至今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去大昭寺的经历,它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由此发生,更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将遭到异化的我重重击中。那是一个黄昏,我被依然保留着藏人传统的亲戚带往寺院。不知为何,泪水从我迈进寺院就莫名涌出。当我见到含笑的释迦牟尼佛像时,不禁失声哭泣,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终于回家了。”不过我立刻感到痛苦,因为听见旁边的僧人用藏语感叹:“这个加姆(汉人女孩)是多么可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