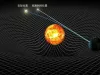(作者提供)
“创新”理念虽然早就由一代宗师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5~1950)在1934年明确提出,但真正发光发亮却是二十世纪末期,当“知识经济”出现之后的事。在台湾,前台大经济系教授陈博志担任经建会(现今的国发会)主委时,曾大力推动知识经济,而促动全球知识经济热潮的重要人物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学者佘罗(L. Thurow,1938~2016)是其中之一。
陈博志教授在2004年5月5日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双月刊中,写了〈佘罗教授知识经济的观念及其在台湾之应用〉这篇文章,推崇佘罗“相当重视经济体系不均衡的状态及其调整过程”,而佘罗就是认为“不均衡的状态是高报酬、高成长的来源”。
“不均衡”的获利论
也就是体认不均衡是获得高额利润的主因,佘罗乃提倡“知识经济”,经由“知识”来创造“不均衡”。陈教授就佘罗的这两个论点,在台湾寻求佐证,并作政策引申。在“善用不均衡来获利”上,陈教授认为台湾历年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是成功的利用台湾和其它地区不均衡的差距,他举出两个实例,一是日治时期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所得、技术,以及气候的差距,提供了台湾农业和农业加工业快速发展的机会。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先进国家之间大幅的差异变成新环境下的不均衡状态,具体而言,工资差距拉大形成开发中国家生产劳力密集产品出口的利基,再因台湾技术落后,而先进国许多技术甚至可免费引进,也都具创造利润效果。简要而言,陈教授认为台湾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可说利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以使人民能利用国际不均衡来赚钱,并促使经济发展的明证,也同时证明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不过,在以自由经济获取不均衡利益时,陈教授也提醒我们,佘罗指出的“消除不均衡有人获利,但也有人受损”之现实,例如台湾廉价产品出口,固然增加台湾就业,也降低进口国物价,对全球整体而言有利,但对生产相同产品的外国厂商却有售价和利润下降之损失,进而使劳工失业。陈教授认为这是很多谈自由经济的学者忽略的问题,因为学术上假设得利者需补偿受损者,但实际世界并非如此。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二十一世纪,以往享受自由化利益的台湾,尝受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进国家利用不均衡获利所带来的损失,失业提升、产业外移、工资下降就是现实问题。
积极创造“不均衡”差距
破解这种不幸后果之道,就是“积极创造”不均衡差距以创造利润,佘罗的知识经济就是主张“以知识来创造不均衡的利益”,而且是以政府的策略为主,选择自己的优势。他特别重视“技术的创新”,于是一个国家要同时培养有创意和创业能力的人,以及不见得有创意却能高效率工作的人。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趋势下,佘罗认为失业和所得分配的恶化很难避免,而政府愈来愈难帮助失业及低收入的人民。
乍看佘罗的分析颇具说服力,而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会导致贫富更不均及大量低技术失业劳工,也是许多舆论的共识。不过,我们或可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先说一个故事,这是2004年在HBO密集上映多次的一部影片,片名叫做Door to Door(中译“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一位天生有缺陷的社区“登门推销员”的温馨故事。当社会快速变化,交通、电信、电脑愈来愈便利,“机器代替人力”愈来愈普遍,登门推销员也难免面临被裁的命运,这位故事主人翁在公司的部门被裁并,他则被当成“受救济者”勉强在仓库一角保有位子,但在受不了被忽视及自卑心作祟下,辞职回家了。
一位从小观察这位登门推销员长大的报社记者,写了一篇专文介绍此推销员,以“一根联系社区成员的心之线”来形容其功用,既触动已成为“现代社区”的所有冷漠、寂寞的住民,也唤醒该年老登门推销员的自尊,更让他领悟到自己的价值,而且重新发现可以扮演的角色,于是不但重回公司,业务更是欣欣向荣。该浴火重生的推销员更借由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帮助,让服务范围及内容更为扩大。这个简单、生动的例子其实告诉世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并非造成“零和”结局,只要有“心”,且真心服务别人,非但不会被淘汰,反而会在现代人愈来愈空虚的“心灵”,找到更宽广的机会。
这个故事也显示任何有心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总能在宽广的机会中寻得自己的利基,也就是找到自己的特质,或者“比较利益”所在,这也是创意、创新的一种,而全球化下的世界其实更为海阔天空,更容易让每个人寻得自己的有用之处。不过,必须提醒的是,在寻觅的转换过程中难免要支付代价,因而平时不要忘记“储蓄”作为预防不时之需,乃是人生必备事务。
爱迪生vs.爱因斯坦
至于佘罗所主张的“创造不均衡”,涉及这样的课题:人际间的“不均衡”或“差异”,或者“创新”“创意”,究竟是“自然长成的”或“政府做成的”?佘罗倾向于后者,因而主张政府以政策来累积知识,来促进创新和营造创意,来推进技术进步,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利诱”,以红萝卜做为工具,而“专利权”则是最显着例子。于是我们看到“科技新贵”过劳死普遍存在,从事创意、研发者也都在压力下痛苦地找灵感。也许不必多说什么,就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两位名满全球的创意、创新、发明者比较,就可见分晓。
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位对人类都有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后者纯真、无私、可爱,但前者则刻薄、自私。关于爱因斯坦,我们可再由前台北荣民总医院教研科医研部郭正典主任,于2004年8月6日发表在《自由时报》,名为〈爱因斯坦的风范〉一文中,记述的1933年爱因斯坦受聘至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的一段佳话见端倪。
爱因斯坦要求“低薪”
爱因斯坦应Flexner邀请到一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作研究,这所研究机构就是后来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当时爱因斯坦要求个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Flexner颇感为难,不只是觉得如此低薪实在是亏待爱因斯坦,而且对其他研究人员又该如何比照呢?于是Flexner一次又一次要求爱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后还几乎是哀求,才好不容易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这也可看出爱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俭朴、简单。
自私的发明家
我们转而谈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对人类有着莫大贡献,我在小学时就被灌输爱迪生是位伟人,为了研究可以废寝忘食,是人类的典范,是位伟大、无私、人格高超的人物。这种刻板印象在1988年却被全球知名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给颠覆了。张教授在1984年2月14日发表了〈自私对社会的贡献〉这篇经济散文,在描述“自私对社会有益”的论点时,深怕读者难以同意,乃举出爱迪生这位家喻户晓的伟人来支撑其论点。
张教授说他在1974年到1977年间,曾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其中对有关爱迪生的他特别留意,因为他也是自小就被老师耳提面命,应效法爱迪生的伟大、无私,为社会贡献。张教授在看过有关资料后,下评语说:爱迪生“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他发现爱迪生的自私,世界少有。爱迪生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至极,对于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下属工作。张教授说爱迪生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每次觉得外人可能偷用了他的发明,就诉之于法。如此一来,爱迪生的发明纵然是价值连城,他死时却不富有,因为打的官司实在太多了。张教授说,有人做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用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到的收入,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可以说爱迪生将财富分享给律师,可惜的是,律师也应是高所得的一群呀!
张教授举爱迪生这个典型的自私者对社会有偌大贡献,来印证“自私对社会有益”的论点,与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在1776年《原富》里所陈述的论调异曲同工,都支持“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由于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于是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不论哪个流派就都将“自利心”作为“人的行为”之准则。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拉高层次想一想,包括爱迪生在内,如果拥有“利他心”,岂非能发明更多、更好的,且有益于众人的新事物?若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能以“爱心”“善心”生产物品,岂不让消费者更喜爱?而且大伙儿在生产时也充满一片和谐、和乐气氛,而宝贵生产资源也会被惜用,当今所谓科技新贵“过劳死”、生活紧张忙碌、压力过重的种种毛病不是就不会存在了吗?而包含爱心、善心在内的产品更能取悦于消费者,报酬怎不会滚滚而来?这是一幅“无求而自得”的美丽画面,也是古人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多么诗情画意,多么沁人心脾,又是多么令人憧憬啊!爱因斯坦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别说爱因斯坦只有一个,一般人做不到。也先不要将“不可能”放在脑中,大家何妨一起来试一试跳脱“自私自利”,换以“无私之心”来待人处世,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看看创意和创新是不是会源源不断滚滚而来?
营造创新环境是创造价值的第一步
再就“专利权”这项当代社会用来刺激创新的热门课题而言,涉及“创意可以复制吗?”这个有趣疑问。我们由一则故事谈起,话说前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在2004年4月3日下午,于日本东京的一场演讲中,透露了一段他拜访雕塑名家朱铭的轶事。
李院长某日专程造访位于南投县清境农场的朱铭工作室,才一进大门,就被朱铭自创的一副对联吸引住。该副对联的大意是说目前博士、硕士满街跑,但真正有知识、有智慧的逸材,堪称千万人中难得一二。
看过对联,李院长进一步向朱铭讨教雕塑技法向谁学习而来?不料朱铭反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学来的吗?这个回答让李院长觉得无地自容,在该次演讲中更坦承自己当时的确提了一个蠢问题。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技术
我乍看这则花絮报导,脑中立即浮现另一个故事。那是大约三百年前,意大利有位识字无几的木匠史特拉底瓦里(Stradivari,1644~1737)。此君例行生活中制作的小提琴,至今仍有数把流传,且被公认为“琴中极品”,台南奇美博物馆就因为收藏其中一把而名闻国际。历年来,不断有人应用显微、化学、数学、电子等等现代尖端科技,尝试制作可以媲美史特拉底瓦里的小提琴,可是都没有成功。
现代人之所以无法复制名琴,不完全是找不到史特拉底瓦里当时所用的材料,主因是不知道如何重复史特拉底瓦里的制作技巧。
这两位东西方的名家,都没受过多少的正规学校教育,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人间极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务,可以说是工作,且是日日夜夜重复进行的。台湾的朱铭,虽然曾追随过两位老师学艺,但在众多学徒中得以出类拔萃,而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应该不是抄袭、复制而来,即便是抄袭,也不可能胜于原作。而意大利的史特拉底瓦里也曾在1666年拜阿玛悌为师学习制琴,但由史特拉底瓦里名琴的无法以现代科技复制,我们更可以领悟到百分百的复制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对于当代“专利权”这个热门而重要的课题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省思,或许其弊会大于其利呢!
学而时习之
此外,由这两个故事,我们也可以思考“学习”的精义何在。朱铭当着李院长的面否认其雕塑技法是学习来的,但他确实是跟过两位老师,而且也开班收徒,难道这不是学习吗?而史特拉底瓦里也曾拜过师。他俩跟随老师做什么呢?一个是“学”雕塑、一个是“学”制作小提琴,而且都跟在老师身边好几年呢!难道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学而时习之”?
在朱铭的心中,“学习”可能是指本章一开头所提,二十世纪末开始响彻云霄的知识经济所强调的“创意”“创新”之意吧?有差异、有特色、被公认价值高应是“创意”的精义,这应不是靠学习可以复制出来的!是“长成的”而非“做成的”。所以,政府若要使用政策,是应该往培育一个适合“长成的”创意或创新环境着手,这不是值得朝野上下有心人士严肃深思的课题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