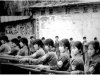张贤亮:文革谈性最安全 越下流越保险
于是,连我九个人纷纷爬上车,先不让我挂牌子,我找了个靠驾驶舱的拐角坐下来。带队的排长站在车头,“嘭嘭”!使劲拍了两下驾驶舱,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我们便向银川市进发了。《地道战》《地雷战》看得次数多了,说“咪唏咪唏”、“开路一麻斯”、“八嘎牙噜”、“花姑娘的有?”这样的日本话是一种时尚。
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战士们意气风发地靠在三面车帮上,御风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颠了不久,我偶然掉过头一瞥,才发现紧靠在我身旁的是个女兵,她穿的绿色军装女裤不但没有系好纽扣,还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裤是侧面开口的,不系纽扣,里面的裤衩就敞露出来了,而这位女兵却连裤衩也没穿。不穿裤衩是农村人的习惯,并不稀罕,一则为了节省布料,二则也没有必要,西北农村人不论男女,晚上睡觉都是光溜溜地钻进被窝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没穿过裤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侧,给已经被激发起青春期骚动的我极为强烈的引诱。别人都站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与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时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肤不止“白格森森”并且细腻光洁,随着车身的摇晃时而紧绷时而松弛,表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弹性。顺着腿部往上看,见到了她丰满的臀部,是标准的半月形,腰肢滚圆而挺拔,乳房高耸,乳峰还微微向上翘起。一身绿军装仿佛无法包束她内在的张力,不仅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鼓鼓的,并且具有一种不知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的杀伤性的诱惑力。多年后,“性感”一词走上台面时,我才领会到多年前见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脸庞红润饱满,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远方眺望,一头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拂,如玉树临风一般。在那时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后附的《毛主席诗词》里,我发现毛主席描绘人物景物的诗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义,那就是“飒爽英姿五尺枪”,其余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概括或水墨画式的写意。这时,我不得不叹服“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准确精炼。她靠在车帮上的姿态,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诗来形容更传神的了,她就是这句诗的形象化诠释,何况她身边真有杆“五尺枪”哩!
路边的白杨树影一段段投射到车上,像飞速闪动的栅栏那样令人目眩。卡车不停地摇晃,我的头不时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车颤动得还激烈。她并不挪开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许她自己并没发现她的裤扣没系好。但这巴掌大的一块女性的肉体,令我生出一种倚翠偎红的柔情,让我想入非非,好像注定我应该和她有段罗曼史,不然这次艳遇便白白浪费了。我后来发表的《土牢情话》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这天真美丽!
没料到卡车这么快就到了银川市西门。卡车停下来按响喇叭,周围人声鼎沸,排长伸长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让路”。我不得不也站起来看是怎么回事。一看,银川西门桥这一片已经人山人海,连西门外的唐徕渠边只有碗口粗的小树上也爬满了娃娃。卡车别想再往前开了。排长下了车,挤进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长也被淹没到人海里去了。战士们个个兴奋莫名,性感女兵高兴地在车上像跳绳似地一蹦一跳。的确,这样盛大的群众场面在南梁农场或说是农建十三师五团从未见过,这预示著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好戏要开场。
等了一刻钟的样子,排长满头大汗地挤回车跟前,骂道,他妈的,扣子也挤掉了!咱们来晚了,公审大会已经开完了,这会儿就等着看枪毙人了。读者可以算算时间,从早上七点出工时开始,我在连部门口等连长和排长争论,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团部政治部耽误了一会儿,然后是团革委会成员讨论,找牌子,换版面,到我们九人爬上卡车颠簸了三十多公里路,车到银川当然已是中午时分了。
排长说西门外就是“杀场”,公审大会是在银川市南门广场召开的(今天那里还是开大会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大队人马正在“游街”,不久就会“游”到“杀场”来执行枪决,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写错了字。性感女兵更兴致勃勃,跳着蹦着说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车被大群人包围,根本无法掉头。
没多久,西门大街上就浩浩荡荡来了大队人马,开路的是几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装战士。那时,解放军、警察、公安人员、军垦部队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学生娃娃、红卫兵等等,服装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至少在我的眼里,一律是绿军装。我说真正的武装战士,是指这些士兵穿的绿军装上佩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手里拿的不是“破枪”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现代化武器。“杀场”居然没有戒严,听任大片人群推来挤去,吉普车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来横着枪杆子将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开出一条通道。吉普车后是一溜大卡车,沿着通道吭吭地开到唐徕渠边一片开阔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楼林立,成了居民区,北面是银川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过去,这里历来是“杀场”,听宁夏的老劳改犯人说,马鸿逵时代曾流行这样骂人的话:“妈拉巴子!把这嘎子拉到西门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枪毙掉。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看出来,集合到这片荒地上来的市民好像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序的。公审大会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横幅标语,可是游街时恐怕没带着,所以“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我不禁想到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口号:“革命,是革命群众的节日!”今天就完全体现出这句话了,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
前面几辆卡车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士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得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妈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非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默默传情的含意。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队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
×美丽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得唾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来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来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闹腾的,早知道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着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这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它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挽,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瓤,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按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
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妖娆诱人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卡车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得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撂在满地西瓜籽的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体行书写的我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得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没有什么比活着并且快乐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们连队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没“婆娘”等我吃饭,我还要等到食堂七点多钟以后开饭才能捧着碗去打,还不如钻进菜地里偷些西红柿黄瓜一类的蔬菜充饥。
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现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时我还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黄瓜西红柿,在小树林中找了块既僻静又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享受。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闹着玩”的文化心态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至今,我回忆起“文革”当然会感到沉重,却怎么也不会严肃和庄重。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见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女童挂着牌子到“杀场”陪绑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几位朋友说“文革”时期也曾在他们那里发生过,毫不稀奇。残忍的事发生多了,竟会冲淡残忍本身,使残忍变成一种常态。你所见所闻“文革”中的事件不论多么古怪离奇,马上就有人会说出另一件事比你说的更离奇古怪,以致你会失去再一次述说的兴趣,这大概也是我们渐渐淡忘“文革”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据说那天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数都给予了“平反”。但我觉得他们的死总比在悲愤中悄悄地自杀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为枪毙他们的时候虽然人声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该死”;二,他们死亡时有近万人来给他们送葬,也可说是很壮烈的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本文亲历历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613/570801.html
相关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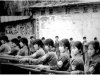



 胡德华:难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胡德华:难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百年真相】影星王莹和她丈夫为何被关秦城
【百年真相】影星王莹和她丈夫为何被关秦城

 【百年真相】毛泽东为何翻脸打倒杨成武
【百年真相】毛泽东为何翻脸打倒杨成武
 吴祚来:温家宝和胡锦涛习近平的差别
吴祚来:温家宝和胡锦涛习近平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