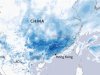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专家陈云霁(左)和哥哥陈天石(右)
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尹希2015年9月初当选哈佛大学最年轻华人正教授后,沉寂数年的少年班再次回到公众眼前。
之前媒体关于少年班的最后一次大讨论,是在2008年。当时,南方周末刊文《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讲述昔日“第一神童”进入少年班后,“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最终遁入空门。
一时,少年班“拔苗助长”的声音一时铺天盖地,不少观点认为,少年班已成“黑洞”,令部分“神童”泯然众生。
真实的少年班,是否是急功近利的试验场?
近日,澎湃新闻走访数名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曾经的江西省高考状元、在中科大与少年班混合编班共同接受少年班教育的刘志峰回忆,“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program(项目)。”从少年班近代物理系毕业21年,李巨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终身正教授,他认为自己在少年班收获了异常扎实的基础理科教育。
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专家陈天石回忆少年班生活说,他们当时一样踢球、看电影、甚至打架,非典时跳窗翻墙到网吧打游戏。
这些少年班成员也不认可“神童在少年班普遍变平庸”的说法。刘志峰每年都与少年班同学聚会,他们“有的是公司董事长、行业的领头人,或是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平均生活幸福指数不错,极少有生活状态非常差的”。
他也略知宁铂近况,他说,当年出家的宁铂在佛法上的造诣颇深,还俗后在学校教学量子力学课、中医课,佛学课,“依然是优秀的大学教师”。
还原真实的“少年班”
1978年,21名15岁左右的早慧少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时间,少年班名动天下。
中科大少年班堪称中国学术精英的黄埔军校。从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庄小威、9月跟随习近平访美的百度总裁张亚勤,到打破了华人年龄纪录晋升的哈佛教授尹希、发明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法的卢征天、发现世界上最小的纳米碳管的秦禄昌、兰亭集势CEO郭去疾,目前,超过70%少年班校友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一般30岁左右就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今,37岁的中科大少年班已从单独的班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院。少年班针对早慧儿童设立,招收年龄16周岁以下的非应届高中生。之外还有针对高考成绩优异学生的“教学改革试点班”、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办学理念也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转向培养“能引领中国发展的创新性人才”。
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负责人刘志峰自称是全世界最了解少年班的人之一。1995年,他以江西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教改试点班(也称“00班”)。
刘志峰那一届,中科大将少年班和“00班”的学生混合编班,共同接受少年班的教育。“这样有利于互相借鉴。年龄大的孩子自制力好、基础也扎实,年龄小的特别聪明、有灵气。”
比他高5级的学长李巨也成长于混编班。回想当年,他说:“30名少年班同学跟30名大两三岁的00班同学混住在一起,一起上课。总体来说,相当友爱,气氛融洽。我中高级计算机的编程技巧基本都是从同学那里学到的”。
李巨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正教授、核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兼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一晃,他从少年班的近代物理系毕业也已经21年了。
他告诉澎湃新闻,少年班的学习节奏可谓相当紧张,可当时他不觉得,“也许是因为除学习没有别的想法和压力”。
大学四年,李巨收获了异常扎实的基础理科教育。“少年班对我科研事业成长有极大的帮助,总体来说应不逊于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program(项目)。”李巨说。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他自愿修习了36门研究生课,这是该校核工系博士学分要求的4倍,涵盖了7个理工系,并且,李巨的成绩单没有B——36课全A。“天赋和勤奋之外,还需要好的运气。”李巨觉得自己运气不赖。
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正教授、核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兼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李巨
“讨论少年班没有意义”
然而,让李巨至今难忘的却是同班“一号学霸”狄雨的一则轶事:“室友狄雨记忆力超好,过目不忘。有次中考,狄雨回寝室后大哭。问之,曰考砸了。不饮不食。相劝良久。后发卷,狄雨仍考全班第一。我等无语。”
狄雨确实也不寻常,读书拿学位如砍瓜切菜。2014年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念完他的学位竟花了差不多一分钟。
刘志峰也提到了狄雨:“少年班确实出了很多奇人,我们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高中时期,刘志峰也曾头顶“聪明人”的光环,进少年班之前,他本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再也考不到第一,成为班上很普通的学生,“整个人的自尊还是会崩溃的”。
这方面,2003级少年班的胡磊万城和2001级的陈天石同样深有感触。胡磊万城记得,同学彼此间的特质差异很大,颇有一些“奇人异士”。而陈天石还一度产生过自卑情绪,“一开始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了,再后来发现同学里有的记忆力特别好,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强,有的反应迅速,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各有所长而已,也就释然了”。
“这社会上一定有一部分人的智力、体力是普通人赶不上的。我们每天要学习到晚上11点,但少年班一定会有些人,成天不学习、踢球,考试之前我还去请教解题方法,他就一边看武侠小说一边写给你,说‘拿去背吧’。”因此,刘志峰认为,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碰到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一定要上完高中三年,反复温习,其实是种摧残。”
少年班为何桃李遍天下
胡磊万城是玩蟹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当初报考中科大少年班,吸引他的是两点:入学一年后自由选择专业;不用再上高三。
少年班四年时光里,胡磊万城多次被震撼“三观”。中科大的风气在思想上推崇自由独立,同时也偏重学术。入学的头两个月里,就连续开设了多场学术泰斗大牛专门针对少年班的讲座和座谈。
2004年的一天,系里安排一位少年的师兄给新生做讲座。“这是第一场不以学术开头的讲座。其中有一段,讲到人生有三大简单易得但极为愉悦的享受,分别和三样东西有关,‘书、食物、床’。师兄对第三样享受阐述颇多,应该是我之前、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公开听过的对性和人生关系的讨论。”那时候胡磊万城刚16岁,因而印象尤深。
而生活上,少年班系里对学生年龄偏小的情况,考虑得很周到,胡磊万城“基本都忘了想家”。但大学毕竟是很多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独立生活,胡磊万城的班里,也有因不适应独立生活举家搬来合肥的同学。
外界对少年班总有好奇,也有诸多误解。刘志峰告诉澎湃新闻,多年来,真正的少年班从未扩容。自科大少年班开办以来,少年班模式一度被众校效仿,到现在,仍坚持开办的却寥寥无几。
“那是因为中科大太牛了,做出了品牌,形成了垄断性。”刘志峰调侃说,“最聪明的人几乎都被中科大弄走了。每一年上清华北大的高考状元,都有前一年被中科大刷下来的,所以少年班的学生基本上是比高考状元还聪明一个数量级。”
而对于西安交大少年班,刘志峰却指出,该模式实为以大学名义招收初中毕业生,“是让学生到大学再念两年高中,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品质也和中科大少年班不可同日而语。”
从入学选拔、课业安排到心理辅导,中科大少年班摸索出一套成熟的体系,采取独立建制、集中培养,不惜成本以书院式为早慧少年提供量身定做的路径。
“中科大少年班多年下来做了很多工作和积累了很多经验。为少年班配备的师长,有相当比重的泰斗,年轻的老师也都是一时之选。”胡磊万城说。李巨也对少年班的用心满怀感激。“如果没有少年班、中科大老师全心全意的培育,没有同学们的潜移默化,不可能会有今天。”
此外,1978年,中科大就施行了“通识教育”,学生先不分学院和专业,打下扎实的数理基础,之后才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平台,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的头一次。
“没有比这更互补、更亲密的学科交叉式的同学互动关系了。”刘志峰感慨,与他同屋的有学计算机、统计,也有学生物、物理的,时常交流,使得他们大大扩宽了视野。“现在,我同学里有牛津的物理系教授、清华的化学系教授,多伦多的地质学教授,我有任何问题都能找他们。”
连刘志峰的毕业论文也是得益于此。在加拿大读计算机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以计算机来研究蛋白质结构,“我的导师只懂计算机,对蛋白质结构其实是不太懂的,后来是依靠当年住在隔壁研究生命科学的同学,他能解答所有生物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我论文生物领域的导师。”
大部分配偶年龄大过自己
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专家陈天石和哥哥陈云霁是少年班历史上不多见的亲兄弟。
按陈云霁的说法,少年班的孩子适合搞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陈天石也赞同,“除了智力的优势,年龄小杂念少,对科学研究的动机和恒心更强大。”
然而,课业之外,这群15岁的孩子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高分低能”。和同龄人一样,他们踢球、看电影、打游戏,甚至打架,而且由于习惯了总和年龄稍大的人相处,他们的心智、思维其实成熟得更快。
有一点可以为证——大部分少年班毕业生的伴侣年龄都大过自己。“并不是恋母情结或是流行姐弟恋,而是他们一直都比和他们大两三岁的女孩子在一起。就像张亚勤比太太高四个年级,年龄却其实是更小的。”
也有逃课的。陈天石的班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拨特别勤奋的,还有一拨特别爱玩,两拨人平时不怎么来往。”陈氏兄弟属于爱玩的那十来个。SARS爆发的时候他和玩伴跳窗翻墙到附近的网吧打游戏。因为逃课,考前必须突击,通宵看书。结果是,由于玩得过于开心,之后陈天石就不太愿意多玩了。陈天石说:“在中科大,老师对少年班的学生还是比较偏爱,不会因为成绩差,就一无是处了。虽然我是一个本科的学渣,但是读研时老师还是认为也许我努力一下还是能有一定发展前途。从这个角度,中科大其实是很好地照顾了我们这样的学生。”
“一大堆人过得相当不错”
跟任何一个班级一样,也有学生无法适应少年班模式的个例。2013年,两起“神童退学事件”相继曝光,17岁考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硕博连读的魏永康,19岁时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被退学;14岁考入沈阳工业大学的王思涵,因为多门成绩零分,也被学校“责令退学”。
对于少年班模式的争议时有发生。2005年,南方周末一篇《追寻昔日神童》的报道引起社会哗然。该文报道了少年班学生宁铂出家的故事。3年后,南方周末又在《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一文中称,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餍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
然而,刘志峰说,宁铂在佛法上的造诣颇深,同样获得了周围人的钦佩。还俗之后,宁铂在学校教学量子力学课、中医课,佛学课。“好的大学一定不会缺少疯子和神经病。我对早期少年班的学生是怀有敬意的,因为他们是改革的先烈。他们曾激起一代人尊重知识的观念,社会和公众为何不能多给予宽容和祝福呢?”
近期,从少年班毕业的尹希以31岁的年纪晋升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打破了华人纪录。消息传来,给同学圈带来了喜庆和振奋。
除了热烈庆祝,已是计算机材料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的李巨还表示,“我强烈觉得社会(人类文明)给我的多,我返回社会的少。希望这个状态在下个十年有所改观。”
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李巨笑称,“对科学家来说,‘不惑’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确实还是经常‘惑’的。”每天游泳半小时帮助减压,从不熬夜,李巨觉得状态不错。
有人问,现今,那些功成名就的名字以外,少年班毕业的其他人如今过得如何?泯然众人,平庸地生活着?也并没有。
刘志峰说,少年班不是有人想象的以牺牲很多人来成就一小部分人。除了为人所知的杰出人才,还有一大堆在常人眼中过得相当不错的人。“我们同学每年聚会,有的是公司的董事长、行业的领头人,或是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取得尹希一样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平均生活幸福指数不错,极少有生活状态非常差的。”
而且,即使最早的一批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目前也才大约50岁,论断为时尚早。十年之后,也许会有更多惊讶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