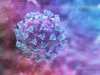我想顺着这个思路,稍引开来谈谈今天国际社会同样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从伊斯兰世界的经验中可以看到,他们现代化运动的失败,不论是何缘故,却终究落入“原教旨主义”的泥潭,专制黩武的军事强人得以利用这股来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资源,则是同他们也曾有过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历史有关,这段可能也是“钜劫奇变,劫尽变穷”的历史,淹没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以至无法提供理性的认同资源。
今天的中国大陆,反身向中国文化要资源的,不仅是上行下效的气功热,也不止于“尊儒祀孔”的袁世凯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独裁政权越来越乞灵于民族情绪中偏狭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倾向弥漫的同时,继续以西方为假想敌,以充分榨取近代以来积累的“屈辱情绪”,并以“西方要使中国保持分裂状态,不放弃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为现实理由,煽动民众的“统一情结”和沙文主义情绪,以保持对东亚和太平洋的进攻姿态,这不仅是要充当区域霸主,也已经显露出步伊斯兰后尘的迹象。
另一方面,“返本”运动又在中国内部制造著汉族之外民族的认同分裂,最明显的自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原教旨”倾向。在台湾发生的认同分裂更复杂,从国家认同裂变到民族认同,以至拒绝认同中国文化;而对台湾本土的认同亢奋,掩饰著“返本”追溯日本的倾向,也是越来越明显。这些群体认同危机将产生的后果,绝非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区域自治的整合以至民族国家的顺利建构,而可能是重演伊斯兰世界的“春秋战国”和波斯尼亚的种族冲突。
回到思想史角度来看,多元化的来临,对近两个世纪的“启蒙心态”是化解还是加剧,值得存疑。至少“西方文化霸权”的衰微,和西方学术界对“启蒙心态”的清理,并未使我们的文化危机稍有缓解,倒是引发了另一个危机向度——“返本论”的崛起。依然“尊西人若帝天”的现代化运动,与“红旗插上曼哈顿”的“返本”运动合流,其激进的张力更高;“反传统”也一变而为以坏传统糟蹋好传统,大陆上未见有一丝儒家“君子风范”来归,却只闻“痞子精神”大行其道。
承担民族认同界定和厘清责任的知识界,或热衷于“后现代”论说,对中国那座文化废墟继续尽情地“解构”,津津乐道于“民族国家话语”对民族情绪的火上浇油;或言不由衷地侈谈儒佛道,以及所谓“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只是鲜少有人面对苍凉、遥远而醇厚的古典精华,以客观知识还原出一个属于我们的起源。
此种困境已非一个“启蒙心态”可以解释,也不只是“尊西人若帝天”那么简单。余英时指出,社会学家研究西方各国民族主义兴起与演变,尤其重视一种更隐诲的心理,即“羡憎交织”——现代化竞争中,落后者攀比先进者而形成的心理失衡:理论上平等的师法对象却永远无法企及和比肩,犹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特别是俄国,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即起步效法西欧,一个世纪后俄国精英自觉已不在英法之下,而整个十九世纪里“憎羡交织”情绪就在他们当中滋长蔓延,因为俄国知识精英们认为西欧并不完美,而他们却追赶不上,马克思主义便在这个心理氛围中生根,并最后在俄国爆炸,于是俄国师法了西欧两个世纪后终于走上了“反西方的西化”——俄罗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超过西方的“资本主义”而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俄罗斯终于“胜利”了。
余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余英时著‘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5月初版)一文中,概略爬梳了这种心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雪泥鸿爪,令人信服地诠释出此种心理将俄国推入“十月革命”,而中国又步其后尘的历史微妙。1981年余英时在耶鲁教书时,发表过一篇“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其中说到:
“近代中国虽屡经战乱﹐但并没有遭到中古欧州被“蛮人”征服的命运﹐在文化上更没有进入任何“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出现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
此文对“五四”的评价﹐也深露“同情的了解”﹐并基本肯定其“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路向。这种态度到八九年他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似有改变,大概因为这种激进化趋势,最终将中国推入“文革”和“六四”﹐恐怕已近乎“黑暗”了。
另一个极为相同的例子是费正清,这位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的“霸师”,震惊于“六四”屠杀,竟在临终前推翻自己以往的看法,著《中国新史》“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余英时作序赞为“学人的良知”。
今天的困惑则是,在一个千呼万唤的“太平洋时代”初露端倪之际,雄视这个大洋的中国,以及剑拔弩张的台海情势,会在认同危机的裂变下,去步伊斯兰世界的后尘吗?
*作者为中国80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运之后流亡美国迄今。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