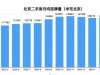18:00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下午6点,27岁金子点亮了酒吧的灯箱,他几乎是北街最早开灯的人。
当金子正努力地卖出一瓶30元的啤酒时,他的顾客正在谈一笔过亿的房地产交易。金子形容这些人是“坐着挣钱的”。“我们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挣得还不到他们千分之一。”
三里屯从来不拒绝任何人,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钱人来这里消遣,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这里可以让人迅速找到同类,也能把另一部分人消磨成同一个样子,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被同化。
酒吧老板David的微信里大概有2000个“好友”,每个发朋友圈的信息都至少有50个“赞”。每晚,他看着彼此陌生的客人交换电话和微信,他很清楚有一类客人在“假high”,但他也要向各种客人打招呼,和他们微笑、握手、拥抱、贴脸,称呼他们“亲爱的”。
Paul并不爱喝啤酒,但现在他会习惯性地点上一瓶自己公司的啤酒。啤酒的泡沫在他的胃里翻腾着,这一年多里,他的呕吐物几乎出现在每个三里屯酒吧的厕所里。一杯500毫升的啤酒,他可以轻松干杯,这份工作已经让他胖了10斤,还有了中度脂肪肝。最近,他已开始测试新人,考察他的“酒品”,而他最初的痛苦也传递给了下一个人。
菜菜一直阻止她暗恋的德国男孩来到三里屯,她的外国前男友最初只是一个羞涩的邻家男孩,但在三里屯,每天都有中国女生请他喝酒。“如果每个晚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女孩,为什么还需要稳定的关系?”男孩和菜菜分手后,他身边从来没缺过姑娘。
但三里屯依然能让Sunny每天出门都能抱有一丝期待感。6点半,Sunny骑上电动车,从东四的一个大杂院出发,她要在7点前到达酒吧开始今晚的工作。而这时已经有两个同事在备料,他们要榨出至少9种水果汁。
Sunny是这家酒吧的调酒师,她已经在三里屯工作5年,称得上“阅人无数”。在她眼中,客人只有两类,“装×的”和“低调的”。她几乎能一眼识破前者,有时,她会和同事打赌这样的客人会点什么酒。“很装的人一般会点长岛冰茶,因为这也许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一种鸡尾酒。”她至少能猜中70%。
7年前,17岁的Sunny刚刚来到北京。那时,她还是一个在王府井卖糖葫芦的小姑娘,一个月能赚700元,每天往返于宿舍和王府井小吃街,根本搞不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但她能迅速打开心扉,在公交车上和一位北京老大爷成为了忘年交,今年过年他们还在一起度过。
5年前她来到三里屯,从酒吧的收银员做起,那时的Sunny还是个慢热的人,她很少主动与客人说话,也不会讲英文。而现在的Sunny会和每个熟客寒暄,开场白通常是:“好久不见,你还在北京吗?最近怎么样?”
她认识5个David、2个Celine、还有数不清的Tony。“这份工作,让我看人看得太清楚,一个清醒的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样子千奇百怪。”Sunny在三里屯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买醉而来,酒吧时光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短暂的休憩,正因为这种短暂,酒吧里的谈话变得不够真实,人们伪装、吹嘘,因为没人在意真假。
至少有70%的客人,Sunny知道对方的名字、工作,但对方究竟是谁,她也说不清。在三里屯,好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又都不怎么认识。
Sunny最晚会在下午两点起床,上班以外,她几乎都宅在家里,她不喜欢一个人出门,“特别害怕孤独,出门必须要有人陪。”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两年,起因是一次分手,“生活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很不适应。”
但Sunny并不是个娇弱的姑娘,每隔几分钟就能在酒吧的二层,听到她在楼下爽朗的笑声。
现在她的收入涨了十多倍,服装品味也从美特斯邦威变成了Zara,但是她再难对人坦露心扉了,“自己的心和别人拉开了距离。就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事。”大多数情况,人们乐于对调酒师倾诉最隐秘的心事,因为对方是一个和自己真实朋友圈不相干的人。而调酒师的心事很少有人问起。客人就是客人,只有极少数会成为朋友。
21:00性是一件简单的事
三里屯的夜晚从9点开始升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某个酒吧落脚,寻找来自陌生人的短暂慰藉。
一到9点,脏街上几家酒吧的音乐会准时响起,这让脏街的声浪瞬间达到100分贝。人们的心脏随着轰鸣的舞曲和电音怦怦跳动。这里有一间名字以K打头的酒吧,提到它的名字,很多三里屯熟人都露出诡秘的笑容,这是三里屯心照不宣的秘密,这个酒吧是大家公认的一夜情“圣地”。
K的舞池能容纳15对“情侣”,他们睁着眼睛在闪烁又昏暗的灯光下接吻,手伸进彼此的衣服,摸索着另一个人的体温,即使你有舞伴,也会有其他人贴近你。一个外国男人对拒绝他的菜菜说:“你不找一夜情,为什么要来这里?”这个困惑只持续了5秒钟,他的眼神便又落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西西厌恶K的音乐,但为了陪朋友,她还是走进了去。西西不挑酒,能醉、便宜就行,于是她在小卖部买了一瓶5块钱啤酒,藏在袖管里带进K。
西西自诩“文艺青年”,喜欢“亚文化”。她今年33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还梳着学生一样的“齐刘海”。她是北京人,有一口浓郁的京腔,一个人住在崇文门的一个60平方米的“城中豪宅”,她喜欢接待世界各地的沙发客,也乐于在旅行中睡在别人的沙发上。她身上有不少文身,一个彩色热气球文在她的右肩上,刻上它“花了3个小时,很痛。”
三年前开始,她常来三里屯,她喜欢和老外们一起站在路边喝酒聊天,“中国人只局限在想一想,而外国人会直接跟你聊天”。她的老外朋友似乎比中国朋友还要多,除了南极洲,每个大洲都有她的老外朋友。“中国人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我常想,如果把两张100块钱放在枕头下,让它们做爱,第二天会不会生出一张20块钱?”
她愿意和外国人成为朋友,有的成为“炮友”,选择标准是“互相没什么感觉,又能聊到一起,还想再见面,就是这样。”年初,她有个“炮友”结婚了,从恋爱到结婚只用了一个月。她多少有点失落,但“这种关系,大家都很有自知之明,一方有了稳定关系,另一方自然就会退出,犯不着有什么纠葛。”
自从大学开始,西西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她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但她“对那些传统的生活没兴趣”,至于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在国企,但很快她便离开了体制。她热衷旅行,又辞了另一份工作后,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人。去年她独自走过至少7个国家,一边旅行,一边为旅游杂志写稿,“我就不能让人管着,有人管我就很烦,所以我不能再上班了。”去年,她还看了32本书,75部电影。这些事,她都是在一个人状态下完成的。
小蕾瞧不起那些借着酒劲儿找一夜情的人,也讨厌“端一杯酒晃1小时,其实眼睛都在瞟男人或女人”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也是对酒的不尊重。“如果喝醉后打电话给前男友,怎么对得起这么多死去的葡萄。”她喜欢这句广告文案,更认为酒后乱性只是一个借口,她觉得“把情绪的释放怪在酒上的做法很无聊”。
这时,一个外国人跑上40级台阶来到一家酒吧,他带着刚刚认识的女孩冲进洗手间,朋友们则在洗手间外列队等候,他们踢门、大笑。30分钟后,他们终于开了门,所有人开始鼓掌,两人则像胜利者一样跳着和欢呼的人群一一击掌。
这家酒吧的吧台上有一樽绿色液体,这是Jim引以为豪的鸡尾酒“宝贝睡3天”。它的配方来自台湾,酒精味道很淡,但一杯就足以让一个不太能喝的人“秒醉”。
两个台湾男孩在这里各喝下3杯“宝贝”,其中一个便瞬间瘫在地上,吐了Jim一身。Jim不得不将他们送回宾馆。第二天,喝醉的男生打给Jim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因为他醒来发现,自己和朋友赤身裸体地睡在同一个被窝里。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男孩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里还曾举办“宝贝”马拉松,参赛者在24小时内喝掉12杯“宝贝”就算胜出,目前只有两个人完成,最高纪录是13杯。他们的奖励是另外12杯“宝贝”。
“不正常”,在这里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Jim所在的酒吧被偷过数不清的摇酒壶和杯子,还有2个灭火器和一个120斤的木雕。也有人偷酒,于是Jim把酒瓶灌满辣椒水。有人刚刚在脏街路口买了一块鸡排,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把鸡排打掉在地,又瞬间跑远。这场景Paul至少见过3次。受害者愣在原地,他的同伴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人去追那个肇事者。
三里屯从来不缺少传奇和秘密。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廉价酒吧,老板是一对40多岁夫妇,胖胖的丈夫永远在监控室里睡觉,精瘦妻子在收银台忙前忙后。经销商一旦有即将到期的酒,便会低价卖给这个酒吧,这里散货太快了。经销商的仓库隐藏在三里屯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这里堆着至少4000箱酒,一箱虎牌啤酒只要80元。
22:00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晚上10点,菜菜化着红唇妆,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和牛仔裤,来到一个高端夜店,人均消费超过600元,但通常女孩不用付钱。一个英国男人走过来对菜菜说:“You look sonormal here。”(你看起来太正常了)因为大部分女孩穿着紧身抹胸裙、高跟鞋,每个女孩跳舞的动作都很谨慎,她们缓慢地扭动出婀娜的曲线。
穿着西装的男人们在卡座上开了无数瓶香槟,陪坐在侧的女孩依然坚持着在冬天露出两条又白又细的长腿,但他们不跳舞也不讲话,大多数时间是在看手机。
菜菜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说几句就会哈哈大笑,有意无意地显示一下自己和酒吧老板很熟。她并不是很能喝,3杯鸡尾酒就能有些微醺,她不喜欢廉价的天堂酒吧,因为“那里的厕所实在太脏了。”她说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纯正的美音,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她的打扮和舞蹈与欧美女孩没有分别,度假时也不会刻意防晒,认为那是“美黑”。
菜菜刚来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三里屯。那时,她被一家知名服装公司派到北京培训,和一个同事住在团结湖的酒店里,但她觉得孤独,因为“谁没事会和同事做朋友”。她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几乎每天都被老板“人格羞辱”。
菜菜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强,她不愿意白天被骂,晚上就在酒店早早睡觉,她要为情绪找一个出口,她发现“去人多的地方心里会好受一些”。
每晚下班后,她就会坐着公交车从世贸天阶去三里屯吃饭,最初她经常自己独自买一个披萨边走边吃,或者一个人在路边吃麻辣烫,后来她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于是就开始主动和别人聊天。
一次,菜菜拿着一个鸡蛋灌饼走在三里屯的路上,一个德国人走过来问她在吃什么,菜菜主动给他尝了一口,之后他们就坐在咖啡馆里,聊了三个小时,至于聊些什么她早已记不清楚。她只是记得,有人陪的时候,生活不会那么寂寞和无聊,哪怕那只是一个陌生人。
那时,她也和男生回家,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菜菜在一次外地旅行中开始了第一次性体验,“那简直颠覆了我的想象,我要把23岁以前浪费的时光补回来。”三里屯的“性”就像大麻一样,一旦开始就会让人上瘾。
回到北京后,这个身高1米57的女孩站在椅子上和1米95的德国帅哥亲吻,一年里,她在15个陌生人身边醒来。“我只是想要帅的男生。”在三里屯,菜菜亲吻了数不清的嘴唇,分别和两个男生恋爱,可两份爱情都只保持了1个月。
来这里的外国人也深谙三里屯各取所需的交易,早已难再付出真心。菲律宾人Peter是三里屯的典型玩咖,一个晚上,这个满身肌肉的男人可以把3个女孩带离酒吧。
23:00比小说还荒谬
千姿百态的狂欢日复一日,人们似乎能在三里屯找到另一个自己,这里成了他们平淡人生中的一次超级冒险。
荷尔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跳跃,当酒精和音乐清空人们的大脑,一些人便获得了白天找不到的存在感。每个月,三里屯的酒吧和夜店要举办数不清的派对,酒吧老板David把一位熟客叫做“派对女王”,因为她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狂欢,她喜欢把外国帅哥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车接车送。她是在三里屯发现有人需要她。白天,她是一位30多岁的高中计算机老师。
晚上11点,新来三里屯酒吧半个月的服务生向军,第一次见到客人跳起钢管舞,那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的五官在闪烁的灯光下模煳不清。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在疯狂的音乐声中,她的舞蹈才显得不那么尴尬。这时,终于有一个女孩跳上另一个酒吧那个将近1米高的舞台,她穿着紧身豹纹吊带裙,在10秒内甩了25次头发,这时音乐已经达到125分贝,聊天变得不可能,但也没人在乎是否要开口讲话。
酒商Paul已经喝下4升啤酒,吐了一次,他希望能卖掉2000箱啤酒,让酒吧经理和他签下一张20万的合约。与此同时,“脏街”路口的桔色成人用品店5分钟内卖出了2254元的性用品。
在酒精的作用下,荒诞的气息在三里屯蔓延。有人带着女朋友来到酒吧,却和另一个女子发生了关系。有人来这里捉拿“小三”,却发现自己和“小三”都不是原配。小蕾目睹了这些荒诞的故事,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写作灵感。这里的故事远比她笔下的小说和剧本荒谬、失智得多。
为了收集素材,小蕾愿意请一些陌生的“漂亮女孩”喝上一杯,听她们讲述自己复杂又极其简单的情感故事。“她们的痛苦,几乎都是因为价钱没谈拢。她们似乎对生活有所误解,以为灯红酒绿才是人生的繁华。”
在一些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尽管每个人的表情都难以辨认,但他们的精神又深层相似。在一家高档酒吧的一个卡座上,至少坐着5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她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尖下巴、大眼睛和饱满的双颊。“这些整过容的脸上,欲望更加明确,她们所有的快感都来自于钱。”
小蕾抽了一口烟,讲了一个从“外围女”口中听来的故事。一个刚刚拿到一笔遣散费的工薪阶层,每晚在三里屯挥霍。10天后,他变成熟客,和其中一个女孩开始了短暂的包养关系,一个月他要付出3万元。而女孩没有想到,这一个月竟会如此“辛苦”,因为男人要求每天见面。其实,这3万元对男人来说是一笔大开销,他希望“物尽其用”。而“一般包养一个月只需要见面三四次,他居然天天有空。”这场交易让双方都觉得亏了本。
2005年,三里屯派出所开始打击三里屯附近的站街女。如今,更多的漂亮女孩变成了“外围”和“嫩模。”在这里,包养关系可以飞速建立。在一家灯光明亮的餐厅里,一个男人一边打量一瓶红酒,一边问站在旁边的女孩:“多少钱?”女孩面无表情地说:“5000块跟你走。”
三里屯恰好能满足一些女孩对金钱的虚荣和攀比。想买一个名牌包,一个夜晚便可以找到男人付款,性是她们最低的成本。
当一些事可以用金钱衡量,三里屯也变得越来越直接,少有羞涩,甚至有人不再费尽心机搭讪漂亮姑娘。酒商Paul走在太古里的东侧,5分钟的路程,他被拦下两次。“大哥,想不想喝酒有妹子陪?只要200块。”在一晚无数次拦截中,终于有两个台湾人被说服了,结果他们只喝掉5瓶啤酒,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就要求他们付款5000元。
龙哥负责给工体和三里屯的夜场摆平麻烦,他手下有一批保安,一个酒吧需要付他1000元才能叫来一个保安把闹事的客人送出门外。
在三里屯,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各种情绪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酒吧经理Jim举办过数不清的狂欢,也举办过难以统计的离别派对。几乎每天凌晨都能见到在街边呕吐的男人,瘫倒在地的女人。冬天,三里屯派出所的警察会把醉倒在地的外国人带回警局,让他们睡一晚再离开。现在,三里屯北街的酒保们统统戴上了“朝阳区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警察给他们开了两次会,让他们戴上了这块红布。
一段时间里,每周都有朋友在Jim的酒吧宣布离开北京,从此这些人将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这样的告别也让40岁的Jim流下眼泪。“有个朋友在北京8年了,现在说走就走,这辈子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
金子今年才27岁,已经觉得生活无望,现在的每一天“纯粹是为了过日子”。5年来,他至少有7个朋友相继离开三里屯,有人开始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人回老家做起小生意。“他们想过正常一点的生活,但三里屯给不了他们,这里好像有今天、没有明天。”
平时不愿意出门的调酒师Sunny最近报了一个拳击训练班,逼迫自己出门。每周她有三个下午的课,两小时的拳击训练,让她又认识了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她觉得很放松,“来这里上课的人就是为了放松、锻炼、发泄,同学之间没有顾虑、没有利益冲突,也不用思考彼此的关系。”在这里,她不需要和别人客套,还能揍别人。
现在,西西更愿意去鼓楼的酒吧,那里有更优质的音乐和更有趣的外国人,而且“大家都不装”。她几乎不再去三里屯,因为“那里的人不在乎音乐,只在乎姑娘好不好看、性不性感,目的性太强。”
2:00疲惫的凌晨
三里屯拥有全北京最长的夜晚,挨着的团结湖地铁站23点45分开出的末班车,永远等不到最后狂欢的人潮。
但有时你能隐隐感受到整个三里屯陷入疲惫。外国人也在聊和中国人一样的话题:雾霾、房子和物价。他们学会讨价还价,不再给小费。王伯的修车摊摆在脏街路口,平均一天会有两个外国人,用中文对他说:“便宜点儿。”
凌晨,在三里屯趴活的出租司机会带走这里的人群,他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呕吐、千奇百怪的痛哭和莫名其妙的尖叫,有时他们会对深夜离开的漂亮女孩开句玩笑:“你下班啦?”即使她是一个正经女子,也懒得做出解释,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人会记住你。
夜半时分,一家酒吧的两个钢管舞女来到吧台,每个人拿走200元,9点到12点她们要表演4场钢管舞。苹果店的保安终于可以坐下来,用iPad3玩斗地主。凌晨2点,另一家酒吧开始了最后一轮接单,一小时后,这里音乐骤停,灯光打亮,客人的表情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明亮,一丝惊慌和失落在他们脸上稍纵即逝。这时Sunny已经工作了8小时,她和另外3位调酒师至少做了600杯鸡尾酒。
小蕾也有些醉了,她想起海子的一首诗,《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里的那句:喝醉酒时,酒杯很安全,心很安全。
这时候,一家廉价酒吧已经卖出240瓶青岛啤酒,700杯Mojito,6袋垃圾摆在这家20平方米小店的门口;在125分贝的音乐声中打瞌睡的向军终于下班。Paul拖着醉倒的朋友企图为他在三里屯找到一间宾馆,但在三里屯1公里内聚集的超过1200家大小宾馆几乎全部客满。最后他把朋友放在一个简陋招待所的地下室。
这时,一个黑人递给小蕾一根“烟”,她吸了两口后直接晕倒,男朋友不得不把她扛回了家,那原来是一种烈性大麻。
凌晨5点,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裙的女孩正在等待出租车,她在零下5度的气温中瑟瑟发抖,她的羽绒服在三里屯至少被偷过两次。这时,菜菜正悄悄离开一个陌生男人的家,她要赶回老家的航班,在那里一切都和三里屯不一样。
早上7点,一个女孩戴着墨镜来到24小时营业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她没有地方卸妆,眼线、睫毛膏、眼影在眼皮上洇开,宿醉带来的头痛正帮助她记起昨晚的狂欢,而2小时后她就要穿好正装坐在国贸的办公室里。
下午2点,Paul的朋友渐渐苏醒,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完全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