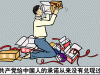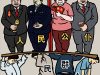冒效鲁,字叔子,晚清末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由上海复旦大学奉调到合肥新建的安徽大学,任外语系俄语副教授。听说他是明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工旧体诗,与钱钟书唱和不绝。到安大后,他写过一首七绝,歌颂鲁迅精神,登在官方刊物《安徽文学》上。一开头的两句是:“身无媚骨奉公卿,笔驶风雷魍魉惊,”传诵一时。不久之后,政治运动一来,系内的好事之徒便结合他平日的“反动言论”上纲上线批判,一口咬定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以歌颂鲁迅为名,行恶毒攻击共产党领导之实,斯可忍,孰不可忍。好在诗人脑勺后的小辫子大把抓,再添一条也无伤大雅。
时隔不久,陈毅元帅驾临安大视察,指名要拜望诗人冒效鲁。这可惊动了大学的党政领导,由校长亲自陪同元帅登门造访,并派保卫科科长站岗放哨。原来陈毅当年任新四军司令员时,司令部就设在如皋冒家的一座庭园,本人也写旧体诗,遂趁便“礼贤下士”谈诗论文。冒氏一向直言无忌,也就趁便翻出“反诗”来向元帅求教,陈毅连称好诗。从此以后,领导和同仁对他都另眼相看。逢年过节,校长必首先登门祝贺。全校上下,人人尊称冒老。
我是一九六二年才有幸结识冒老的。前一年,我在举世闻名的清河农场劳改,饿得奄奄一息,经妻子从合肥赶到北京奔走,终于得到“保外就医”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到安大家中,由妻子抚养。六二年秋,我当上外语系“临时工”,教高年级英语,并参加“统战对象”的政治学习。我头上戴着“极右分子”和“劳动教养分子”两道紧箍咒,学习时除了检讨不离口,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而冒老哩,谈笑风生,放言无忌,与我的寒酸相真有天壤之别。私下里,我们倒是一见如故,加上我当年在北京也和钱钟书先生有过一些交往,因而又多了一重关系。有一天,我盛赞他的两句“反诗”音韵铿锵,气势磅礡,极之令人振奋。他呵呵一笑,说鲁迅若是不死,五七年不打成“右派”才怪哩!又说,自己居然逃脱一顶“右派”帽子,可能是祖先积德吧。
无奈好景无常。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冒老是全校首先抛出的头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接着是批斗会、抄家、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劳改、等等、等等。我因为只是一名“临时工”,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毕竟也不过是一头“死老虎”而已,因此,我竟然官封“牛鬼”学习小组长。外语系教授、老讲师衮衮诸公,不下一打之众,都归我“领导”。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所谓学习就是人人交代、检讨,互相揭发、批判。听冒效鲁(已经无人称他“冒老”了)检讨交代,几乎是一种享受。他的开场白总是:“我姓冒,冒充的冒。我是一名死不改悔的反动知识分子,却冒充什么教授、诗人,真是恬不知耻。”交代起历史来,一口“京片子”,侃侃而谈,毫无愧色。可是结尾一定加上:“我的罪行罄竹难书,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有一天,会下我问他:“老冒,你一死还不能赎罪,欠下的罪谁来还呢?”他一面抽烟,一面说:“唉,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嘛!还不完的债还可以一笔购销吧。”随即哈哈一笑。
一九六八年冬,我和他一起作为“校管专政对象”,由红卫兵押送,随全校三千“革命师生”到和县(古和州)乌江参加“斗、批、改”,我们这号人就是“斗、批”的活靶子。经过半年的折腾之后,我们两人被分配到南庄生产队,按“物以类聚”的原则,住进富农金家大嫂家一间屋子里,由红卫兵陈宇负责监管。小陈是俄语专业学生,淮北农家子弟,粗眉大眼,秉性耿直,不时和工宣队师傅发生顶撞,却好与老“牛鬼”谈诗论文。我和老冒,身困“牛棚”。居然可以放眼古今,与小牧童言笑无忌,也算人生一乐也。
一日,牛郎把两头老牛赶到霸王庙去放牧。老冒也不过六十来岁,却故意摆出一副老态,步履蹒跚。恰好庙前路面年久失修,凹凸不平,他失足摔了一跤。小陈慌忙把老人家扶了起来。诗人脱口而出念道:“霸王庙前出洋相,教授原来是草包。”我也未加思索续了两句:“牛鬼蛇神我不要,滚回人间去改造。”陈宇哈哈大笑,连声说:“妙!妙!妙!”当天又到同学中去传播,后来因不抓“牛鬼”思想改造、散布“反诗”而受到严厉批判。
一九八零年,事过境迁,我重返北京任教。一九八七年,应邀返安大讲学,冒老携陈宇来宾馆访谈。冒老并不见老,谈笑风生,豪情不减当年。小陈已成家立业,任职数学系,对冒老执礼甚恭。谈话中提起霸王庙之行,陈宇一口气背出了那首“反诗”,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我因工作关系匆匆返京,行前到冒府向冒老和夫人告别。他说希望下次来多住几天,好好神聊一下。不料次年春,他就因心脏病遽发而弃世了。后来听说他的子女已将他的诗集付梓,至今尚无缘拜读,不知这首“反诗”收进去没有。